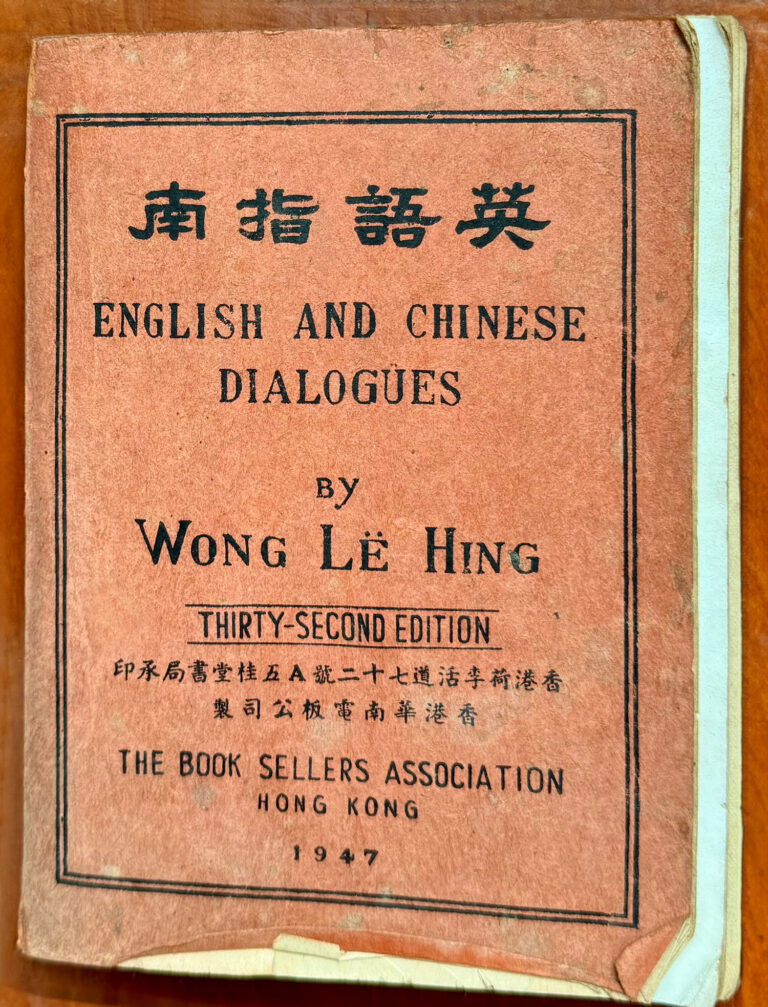編按:今年不僅是金庸先生誕辰百年,也是「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誕辰百年,適逢此機緣,本刊特組織專題,以茲紀念。本版主編潘耀明綜談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俠亦文」的好朋友之間的惺惺相惜和文緣糾纏,並寄望香港對梁羽生百年誕辰應予以重視。梁羽生為了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將自己的文學素養、對歷史的研究和各種雜學加以運用到寫作中,為武俠小說帶來一番新氣象。文學博士陳瞻淇致敬這位「俠情遺韻在人間」的「博觀約取真才子」。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陳墨析論梁羽生對新派武俠開山之功與重大影響、作品中文人小說和成年人的童話之特性,以及一次與梁羽生相見、同行、對談的難忘經歷。
沒有梁羽生的日子●潘耀明
今年有兩個武俠大師誕辰一百周年,一個是金庸,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另一個是梁羽生,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梁羽生的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寫於一九五四年,一炮而紅;金庸《書劍恩仇錄》於一九五五年開筆,一舉成名。梁羽生一九五四年開始共寫了卅五部武俠小說,金庸一九五五年開始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
從以上簡單資料的臚列可知,梁羽生是先於金庸一年寫武俠小說的。以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而論,非梁羽生莫屬。
公道地說,沒有梁羽生也沒有金庸。金庸是後來者,而且是後來居上的。金庸在梁羽生逝世時擬了一段梁羽生的話說:「明明金庸是我後輩,但他名氣大過我,所有的批評家也都認為他的作品好過我。」雖是金庸寫的話,卻說到梁羽生的心裏去了。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梁羽生對此一直是忿忿不平的。他曾化名寫了〈金庸梁羽生合論〉,用以揚梁抑金,大大吐了一口烏氣。只是這篇文章後來被人戳穿了,對梁羽生來說,就有點不好玩了,不免為人所詬病。平心而論,梁羽生的舊學根柢是比金庸要好,詩詞歌賦楹聯樣樣精,這是金庸自己所承認的。
金庸曾寫道:「後來他(梁羽生)應《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兄之約而寫《龍虎鬥京華》,我再以《書劍恩仇錄》接他《龍虎》之班,我們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後,陳凡接寫一部武俠小說,我們三人更續寫《三劍樓隨筆》,在《大公報》發表,陳凡兄以百劍堂主作筆名。武俠小說不宜太過拘謹,陳凡兄詩詞書法都好,但把詩詞格律、國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俠小說上就不大合適了。所以他的武俠小說沒有我們兩個成功。」金庸說陳凡武俠小說寫得不好的毛病,或有他對梁羽生武俠小說借山打石的隱喻,梁羽生武俠小說也有用典過多的毛病。
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孰優孰劣,其實讀者最是心水清。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梁羽生是開創新派武俠小說先河的一代宗師。他的武俠小說沒有金庸寫得好,但他的作品也曾擁有廣大的讀者。有一次文友相聚,談起林青霞與張國榮主演的《白髮魔女傳》可謂雙劍合璧,端的是神乎其技,特別是水畔挑情的一幕,看得人如癡如醉。我當場表示作者梁羽生也應記一功。
令人遺憾的是,今年也是梁羽生誕辰一百周年——金庸先他半個月而生,在梁羽生寫作及工作大半生的香港,卻乏人提起他,無聲無息。從政府到民間,對金庸百年誕辰的慶賀活動鬧得沸沸揚揚、熱火朝天,對梁羽生竟然隻字不提,令人大惑不解。倒是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做了一場「百年梁羽生.永存俠影在人間——紀念梁羽生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稍可告慰這位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地下之魂!
有南京雕塑家陳建華,通過鋼琴大師劉詩昆轉達說要捐贈一座金庸雕塑給香港文學舘,我讓劉大師代轉話情商陳先生再造一座梁羽生的雕像。這位藝術家果然爽快,一口答應,在很短時間內雕了一座梁羽生雕像,讓這兩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俠亦文」的好友在香港文學舘並肩而立,共話桑麻!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高72厘米 青銅 2024
(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
孤懷統覽任平生——寫於文統公百年誕辰之際●陳瞻淇
北宋易學家邵雍曾有詩句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揮麈時。」套用至陳文統先生之創作,可稱為「生公非是愛武俠,俠是生公揮麈時」。
博觀約取真才子
陳文統先生學識淵博,諳熟歷史、詩詞、對聯、掌故、圍棋、象棋等,是著名作家、楹聯學家和棋評家,於文辭一道涉獵極廣。數十年來在報紙上開設多個專欄,除武俠小說上千萬字外,其各類專欄文章亦上千萬字之巨。
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封劍,封的只是三十年來的「筆蕩江湖」生涯而非就此封筆,仍然繼續數十年來的文史小品寫作,陸續刊載於香港《大公報》、《香港商報》、新加坡《星洲日報》等,筆耕不輟。他並未另起爐灶而獨掌一門,而是遠離政治和商業,如中唐元白「元和體」般,「其間感物寓意,可備蒙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粗,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由此陸續如寫武俠小說般刊發,再結集出版,有《筆.劍.書》(一九八五)、《筆不花》(一九八六)、《名聯談趣》(一九九三)、《筆花六照》(一九九九)、《筆花六照》(增訂版,二○○八)等。
先生用功最勤、貢獻最大的是楹聯的創作與研究。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設了三年四個月的每天見報的「聯趣」專欄,後結集為《古今名聯談趣》(一九八四),《名聯觀止》(增訂版,二○○八)分上、下集,《名聯觀止》(二○一七)增補《香港商報》的「聯上趣」專欄內容而使其「聯話」更為完整。先生武俠小說回目精工巧妙,可作為名聯集錦品鑑。
先生長於詩詞創作,僅小說中的開篇詞、終篇詩及書中間涉詩詞便足結成厚重專集。故此乃有二○○八年楊健思輯錄之《統覽孤懷——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一書,分為「少年詞草」、「彈鋏歌」、「劍外集」三部分,選錄先生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初期的詩詞作品、武俠小說中及此外的部分詩詞和對聯。先生知交鄺健行教授在該書序中特地提到:「總覽先生著冊,多納詩詞。所以抒角色之感興,所以助情節之推移。非撏撦於義山,乃推敲之旡本。風貌去昔賢,未逾尺咫;文辭見他作,頗訝馬牛。蓋先生少炙名家,早通律調。每能寄意,尤擅倚聲。往往搖曳清泠,飛冷香於秀句;嘯吟棖觸,憶故劍之平生。至味堪尋,一時莫比。然而雖遵章回之軌轍,亦寓時代之精神。……若夫先生聯語之雅文律切,回目之工穩意賅;此特詩詞之餘藝。茂根而遂寶,沃膏而曄光;可以不煩論議者矣。」結合該書收錄詩詞統觀之,先生詞宗南宋白石、玉田以來的清空一派,古雅峭拔,清麗婉約,在意象、色調、抒情方式上獨具一格,展現出狷潔的文化人格。先生在小說正文中大量運用詩詞楹聯(包括小說名與回目),不僅文采斐然,對渲染環境、交代背景、促進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等都能起到推動作用,甚至成為情節轉捩關鍵,並且平添了文人雅致,提升了小說意境與格調。尤其是開篇詩詞或者結尾詩詞,都能奠定全篇基調和總結提煉全篇主題,有意味深長、韻致悠遠之美學意蘊。
先生採用多個筆名,撰寫各類文史小品。比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開始使用「陳魯」的筆名,用於圍棋、象棋的棋話與棋評,出版有《穗港棋王會戰紀詳》(一九五五,署名陳魯,與王蘭友合著)等;一九八○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以「時集之」的筆名在香港《商報》開設專欄,其間一九八六年一月初至一九八七年五月底的「摘錄評點《金瓶梅》」專欄以每日一篇的量累計三十二萬餘字,後結集為《梁羽生閑說金瓶梅》(二○○九);四百多篇談論民國時期詩詞作品的文章後結集為《梁羽生妙評民國詩詞》(二○一六)。
其他筆名,如以「梁慧如」寫歷史小品,以「馮瑜寧」寫文學隨筆,以「李夫人」之名主持「李夫人信箱」等,這些散文、評論、隨筆、棋話,後結集為《史話一千年》(一九五四,署名梁慧如)、《婚姻與家庭》(一九五五,署名馮浣如)、《文藝雜談》(一九五五,署名馮瑜寧)、《人生與友誼》(一九五五,署名馮浣如)、《中國歷史新話》(一九五六,署名梁慧如)、《三劍樓隨筆》(一九五七,與金庸、百劍堂主合著)、《李夫人的信》(一九五八,署名馮浣如)、《古今漫話》(一九六九,署名梁慧如)、《人生的探秘》(一九七二,署名馮浣如)、《文藝新談》等。此外還有「馮顯華」、「幻萍」、「佟碩之」、「鳳雛生」等筆名。
境界始大開新派
先生早年立志從事文藝工作,後來也以文藝小說的標準來創作武俠小說。
他曾指出武俠小說完全可以符合文藝小說的要求,即反映時代、塑造典型人物及藝術感染力。怎樣才能寫好武俠小說?「寫好武俠小說並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備相當的歷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識,並有相當的藝術手段、古文底子,而且還要懂得中國武術的三招兩式,才能期望成功。」撰寫者的創作態度應當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的邀請作「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的演講時,介紹了自己創作武俠小說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時代的歷史真實;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先生一貫主張,武俠小說的創作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和文化儲備。僅僅把文本和形式當作突破口,對傳統文化、對歷史、對文學沒有真正認識的作者,是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來的。從這一點反觀先生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會發現既繼承了傳統小說的形式和審美,又摒棄了傳統武俠小說一味復仇、嗜殺的傾向,將現代的歷史政治觀念融入武俠小說;不僅將傳統小說中詩詞、回目等藝術形式大加發揮,而且提出「以俠勝武」的創作觀念,賦予「武俠」新的含義,將武俠小說這一通俗文學類型提高到一個新的藝術境界。
先生撰述武俠小說時受到當時文學政治觀念的影響,創作中展現出以人民性為本位的俠義觀,幾乎每部都在明確的歷史背景下展開,從唐至晚清,搭建起屬於自己的宏大江湖世界和歷史譜系。主人公多能做到俠義精神與歷史責任的統一。所以他筆下江湖義士較少,憂國憂民、為國為民的歷史英雄較多,一新明清以來白話小說英雄人物為官府、帝皇權臣分憂之風氣,極具現代意義。由此,他筆下不僅有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名士遊俠,亦如《紅樓夢》般刻畫出一批智勇美兼具並勇擔重任、遠勝鬚眉的女性形象。
但開風氣不為師
與此同時,宏大敘事下乃有師老兵疲之弊,比如模式化的創作傾向,主題和人物性格的單一,對人性世態的描摹偏於浪漫而缺深刻,傳統白話小說創作那種枝節曼衍、說教甚重的筆法在其後期創作中也多有體現,等等。
中國武俠文學研究專家陳墨在二○○九年緬懷先生的〈情懷梁羽生——莫道萍蹤隨逝水〉中寫道:
閱歷深厚而才華橫溢,偏率性懶散而不善經營,的確是生公大俠為文和為人的重要特徵。若善經營,其小說藝術張力可發揮到另一重天地;若不懶散,而對其小說進行必要的修訂整理,則其小說必更少瑕疵而更多精彩,俠迷梁粉必有更多可探討可讚歎的話題。小說之內如此,小說之外亦如此,梁園雖好,其值不彰,未嘗不是缺少內外經營之故。
這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心態,學養豐厚、才氣非凡卻始終心有旁騖,終致先生僅成就一代武俠小說宗師之名。
先生心思純摯,秉性率真溫厚。中山大學冼玉清教授說他「忠厚坦摯,近世罕見」,可視為不通世務的另一說辭。香港詩人舒巷城贈詩「裂笛吹雲歌散霧,萍蹤俠影少年行。風霜未改天真態,猶是書生此羽生。」詩中的末句,令先生大呼「知我者,巷城也」。識者則以為如此書生品質,做學問或寫詩或許是美質良才,作為小說家則未免有所欠缺,這也許就是先生武俠小說中創作主題、人物刻畫、情節場面等過於單一的根源所在吧。再就是陳墨先生在《香港武俠小說史》中所指出的:「在獨立意志、獨立個性追求,以及獨立思考勇氣、習慣和能力等方面,梁羽生與金庸有很大不同」,加之創作中後期如同還珠樓主般魚龍曼衍,互文迭出,終致藝術表現效果打了折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期找不到修訂出版《武林三絕》的恰當方案。
俠情遺韻在人間
先生曾有集句聯:「俠骨文心,雲霄一羽;孤懷統覽,滄海平生。」此聯既暗嵌「文統」、「羽生」之名,又是他的人生寫照。「俠骨文心」為其武俠主題亦寓其為人要義,「孤懷統覽」見其廟堂之高廊廡之大,將其平生情懷抱負、功業感慨悉納此聯。他開創了一個新武俠繁榮的時代,是一位真正彰顯中國武俠文化的大師。
二十年前,也就是二○○四年六月,先生在《筆花六照》再版後記中回顧創作生涯,寫道:「往事並不如煙,要說是說不完的,能說多少就多少吧。這正是:舊夢依稀記不真,煙雲吹散尚留痕。」話語一如既往的低調,卻絲毫不妨礙他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以及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文學博士、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