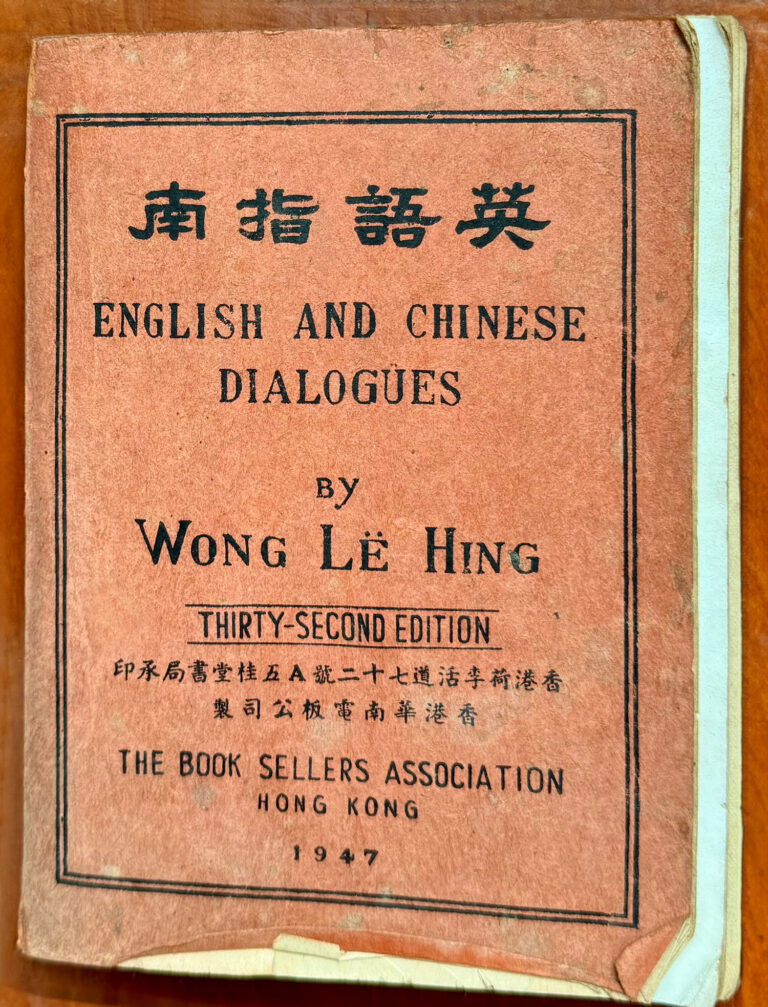不是你一個人活得喪喪的●張 欣
前幾天有一個輕鬆的聚會,吃東西閒聊那種,而且是居家沒有著裝要求,一開始大家都興高采烈,吃完飯集結在茶桌上展開深度聊天,發現每個人都很喪。有正在離婚的,有家中老人癡呆的,有自己身體亮起紅燈的,有重度失眠的,有跟頂頭上司極度對抗又不能辭職的,還有爭奪遺產打官司的,以及一個朋友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實現了夢想輕飄飄來一句那不是我想要的。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大嘆苦經,因為我是前輩嘛。
每個人的故事都有一匹布那麼長,我想說的不是比慘,而是怎麼涼拌。曾幾何時我們都「凡爾賽」過,對別人的「凡爾賽」也非常上頭,感覺自己活着就是給偉大的時代抹黑,本以為疫情是最糟糕的,內心盤算着怎麼把所有個人失誤都推在口罩上,再也找不到這麼合適的鍋了。萬萬沒想到反而是疫情之後情況急轉直下,經濟一路下沉,各種爆雷、倒閉潮、失業潮,然後就是集體迷茫。
那麼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故事當然不全是環境造成的,但是以往的順勢順境會自動遮蔽掉一些不堪和矛盾,因為人意氣風發的時候容錯率高,現在不行了,那些負面的問題顯得格外突兀、顯眼,讓人無法忍受。
然而不知道為什麼,我又會感到一種別樣的輕鬆,尤其是朋友們都困在煩惱中,更顯得這才是真正的生活,是生活本真的樣子,家裏永遠是亂亂的,自己永遠是氣急敗壞的,各種事滿頭包全部等着你去處理。
這不是矯情,正如你爬山、健身、慢跑很累很累換來的是內心的輕鬆,你放棄優渥接受挑戰得到的是精神的解放。現在是我們都不用那麼劍拔弩張爭當成功者了,終於可以喪喪的了。
當你扛過最艱難的時刻,才發現自己是真的長本事了,進步了成熟了,不再是那個有車有包便「剪刀手」的小孩子了。
有人說時代的紅利都被我們吃完了,那麼好,從現在開始我們將不再欣賞夢幻製造夢幻,不用裝出吃不完用不完的樣子,不用粉墨登場,我們將記住羅翔老師說的:「請你務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萬次毫不猶豫地救自己於這世間水火。」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鍾二毛的「新南方寫作」與其不可承受之「輕」●伍 嶺
今天我們談論「新南方寫作」,批評家們都有各自的看法。顯然,這是當代文學討論中避不開的話題。什麼是「南方」,什麼又是新的「南方寫作」,它受地域的影響嗎?自改革開放以來,「流動的南方」就一直是包容、自由、向外走的姿態,在此經驗下的文學創作也自然是開放性的。我一直不把「新南方寫作」視為深圳或者廣東等的地域性概念,它只是借在這個地域下形成的經驗來寫某個群體或者人類的際遇。我想以三位深圳作家:鍾二毛、蔡東、林棹的作品淺淡「新南方寫作」的深圳特色與經驗。
本期我們先來聊一聊鍾二毛。
近期,鍾二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說集《晚安》,這本中短篇小說集一共收錄了十篇作品,聚焦城市中產階層,從職場、購房、育兒、養老等深具社會性的主題切入,觀照他們的生存與精神困境。這些主題以及鍾二毛通過文學來延展的社會問題是屬於南方或者深圳的嗎?顯然不是,它放在國內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需要關切的,哪怕放之四海,也是具有國際視野的反思。我們常說文學的時代性與現代性,《晚安》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那麼它在「新南方寫作」的概念裏又是什麼呢?
本文重點以同名小說〈晚安〉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晚安〉講述了一位患有絕症的母親不堪病痛的折磨,請求自己當刑警的兒子給她一個安樂死。在這個過程中,母親講了七個關於死亡的故事,而這七個故事既是母親對人生的回顧,也是對求死的嚮往。兒子大毛始終平靜地面對隨時到來的末日,但他的平靜就像他每日為母親燒開水一樣,水在壺裏滾燙翻轉,咕嚕咕嚕的低吟,只是悲痛一直被壓抑着。壺本身的「冷漠」,折射出在生死抉擇面前,在傳統孝道的陰影下,無可奈何的堅強。
最後時刻的到來,「(母親)這一絲笑容,彷彿把過去所有的痛苦都抹掉了。這一絲笑容,似乎意味着一切從零開始。」鍾二毛是一位在描寫上非常細膩的作家,此刻的「從零開始」是讀者經歷過七天的痛苦掙扎後一同面向「新生」(死亡或告別痛苦)的開始,我們似乎可以平靜的接受這一切了,但依舊像壺裏的水一樣壓抑着悲傷。
鍾二毛寫,「我把母親抱在沙發上,坐好」,他一直在強調「坐好」這個詞,是因為母親此前因為疼痛只能跪着,但這最後的時刻,要讓母親「坐好」,不僅給予母親最後的尊嚴,也是在不斷加強自己內心的穩,生死離別之際,要把最好的安寧留給母親,所以要穩。
鍾二毛還設計了沒有標籤的藥瓶子,描寫了母親黑洞洞的嘴,也祈求這些藥丸、水啊,都能慢點再慢點進入母親的體內,這最後的母子時光,是鍾二毛定格在文學裏難捨之情,也是讀者無法言說的告別之痛。
身在深圳的鍾二毛和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一樣,皆為遊子,儘管這篇小說未更多提及遊子的心境,但通過與母親的告別,也完成了對遊子的鄉愁、親情與無助的空洞心態的深層且克制的關照。這篇小說名為「晚安」,也是對文本內涵的特別的定義。如果你通讀這本小說集,就能體會到這一點——晚安,在都市裏,甚至在南方城市中是習以為常,甚至有些輕盈的短暫告別語及祝福語,但鍾二毛將此用於「死亡」的主題上,並統領整本書的主題,更體現了他的特別之處——在描寫某個群體的精神困境時,借用了「輕」來反襯生活的「重」,那麼〈晚安〉也好,還是集子中的其他作品也好,都在述說人間漂浮下的不可承受之「輕」了。
(作者為《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明報特輯部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