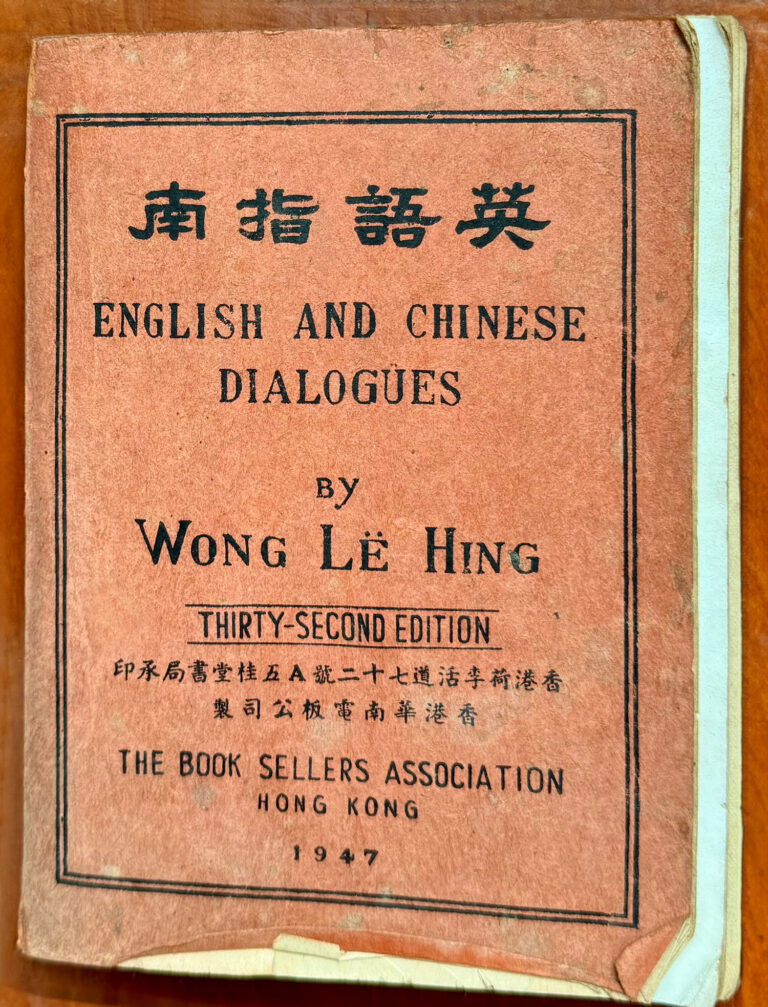太陽正好,赤條條地歪掛在那,又將光端端地散射下來,遠處那架黃土山被抹得通紅,殘陽如血,景物也如血。
黃昏這時,很美。
曾一度變得暗淡如秋的我,獨自坐在那痛苦的思想,一直想得頭破血流,但最後我到底是一無所獲。突然之間一陣暴躁、煩悶的情緒湧上來,以至忍無可忍之時,我將那杯泡得發黑的茶水憤然擲於地上,結果是杯子破碎,茶水尋找到一條路開始默默地流淌,沿路將還沒來得及熄滅的煙頭哧哧地湮滅。我鐵青着臉,走到牆上掛着的那扇巴掌大的鏡子前,臉無任何表情,不屑一顧地讓目光過去,無限輕視地看自己生自己氣的樣子,那樣子很不讓我滿意。我深歎一口氣:他沒來。
昨天是我結婚的日子。早在二十幾天前,我就給他前後發了兩封邀請信,只是到今天還不見他的影子。我無限傷感,他是不是因為他結婚時我沒有去而記恨我了?正當我很悲傷地忐忑不安時,木門開始咚咚震響,有人砸門。我拉開一看正是他!這位自遠方而來的老朋友,和我相互間淡然一笑,小屋裏便立刻有了一股看得見的暖色調。陽光擠滿了整個房間。
這個令人激動的七月,使我顧不得自己的新婚妻子,要和朋友去看山。那山上有太陽——太陽下有一個大水壩,水裏又浸着顆太陽,濕漉漉的沉到水底,將水染紅了紅紅的一壩水。情緒在這一瞬間是如此的愜意。我們同時感覺到。
「日子過得還好吧?」
「還好。」他瞇着雙眼。
「老婆還好吧?」
他沉默無聲。猛然兩肘撐地倏地站立起來,將瘦得誰都會可憐的肚皮努力着鼓起來,兩手指指。我意會到了他所示的含意,我彷彿看到他老婆肚子裏那個活潑的太陽。
「有聲音嗎?」
「咕咕的。像一管生了鏽的法國小號聲,是很能讓人感動的。」
我呆呆地任意去想像他這時的感覺。
遠山上,一位喊山的牧羊漢執把鞭子,在胡亂地漫着沒有水分的乾巴巴的花兒,聲音直勾勾的:
太陽落山一會了,
看不見阿哥的影子;
尋不見阿哥我不走,
我只有這一點本事。
這位朋友斜瞅着那顆太陽,嘴裏叼着的煙頭忽然一亮,我忽然感覺到離我們很近的太陽也忽然一亮。他的臉是瘦黑了,鬍子長得野草一般纏繞了滿臉,那兩隻眼睛卻很精亮。我知道他這幾年為自己的事費了心了。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衝我嫣然一笑,說:「人受點磨礪也好,每個人的日子都是這樣的。是吧?」
「是的。」
「喂,哥們兒,咱倆比打水漂吧?看誰打得多,誰多誰這一輩子就有大福。」
他是一個在山溝溝裏生長的養子,嘗夠了人生的艱難,靠自己的能耐上了三年師專回去後,早早地和一個看上他的丫頭結婚了。結婚時他滿懷信心地叫我去湊湊熱鬧,結果他這個最引以為是知己的我沒去。我知道他不會原諒我的,於是我每天都在懺悔,似一個精神病患者。今天他高高興興地突然姍姍來遲,我也大為感動。
小石頭片都打出去了,沿平靜的水面輕輕地跳躍着前去,如一顆顆小小的串起來的太陽,泛着紅光。
「你怎麼比不過我了。」他看起來很興奮,我知道我是有意不好好打,他迷信自己的話。「你為了讓我高興窮裝蒜!生活對我畢竟是嚴酷的啊,我自己都無法改變,你他媽的能幫我改變?」他惱怒了,揪住我的頭髮,朝我臉上猛砸一拳。他那雙曾吃過苦的手真有分量,我眼前金光四閃。
太陽破碎了,變成了盛開的花,我閉上了眼睛,金光是不閃了,腦袋卻不停地「嗡嗡」作響。
他愣着眼坐在一抹土坎上。那太陽是落窩了,餘暉卻揮灑自如。將流血潑了滿山,山便顯得很悲傷。
水呈暗了,土黃土黃的像撒了一層黑玉,四周無風吹來,水便寂寞無聲靜靜的。遠處的黃土山不黃了,則是一片朦朧的青黛色。我們的心卻在劇烈地跳動,黃昏的眼睛看着我們不眨動霧狀的睫毛。
「給你說句實話吧,我老婆生孩子時死了,都死了。」他聲音嗚嗚的。
「什麼什麼什麼……」我徹底清醒過來。黃昏彷彿又亮了許多。
遠天傳來一個尖細的雲雀聲,聲音淒慘得掉淚。這時,我不知所措,安慰全是些空洞無物的東西,他也很不需要我採取這種他一貫認為是虛偽的方式。但在沒有任何辦法之下,用安慰試探一下吧,總比不試一下的好。我走過去覺得路很長,一直延伸着下去沒有盡頭。
「哭一場吧……」
我的話音還沒散完,他抱住頭便委屈地嚎啕大哭,好不淒涼。唉,這個從沒掉過眼淚的山漢喲!
黃昏好像又深沉了一截,被捂了眼睛似的,金黃的淚痕貼在天際。哭聲終於止了。他沉穩地走到我面前,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臉上流露出一絲對我依舊信任的微笑。我的靈魂在黑暗中狠狠地顫抖了一下。我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
「重新人生!」他說。
「重新人生!」我說。
兩雙手在昏暗裏緊緊地握在一起,有燙人的熱流穿越了我們的軀體,似電若火。眼睛們在這黃昏中閃爍出光亮,閃爍出堅毅。我們看懂了各自的眼睛。
太陽回家了,今天的黃昏是回不來了,但我們深信,太陽明天還會升起。
黃昏的眼睛終於又亮了,而且亮了一大片,閃着璀璨的白光。 (作者為珠海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說集《白太陽》、散文集《心靈的邊緣》、《左邊狐狸右邊葡萄》、詩集《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見於《中華散文》、《廣州文藝》、《雨花》等文學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