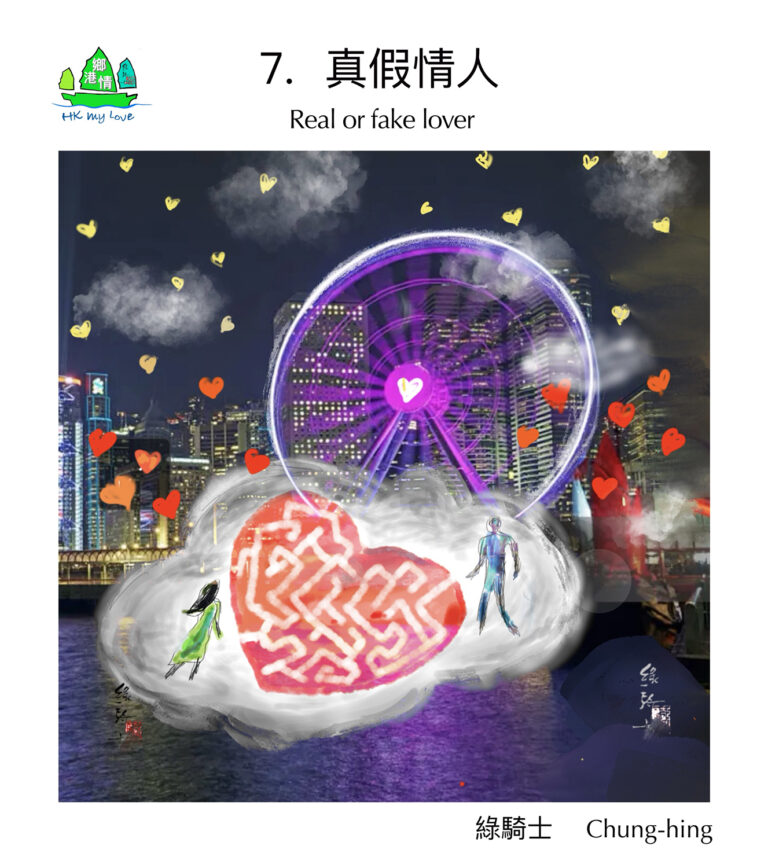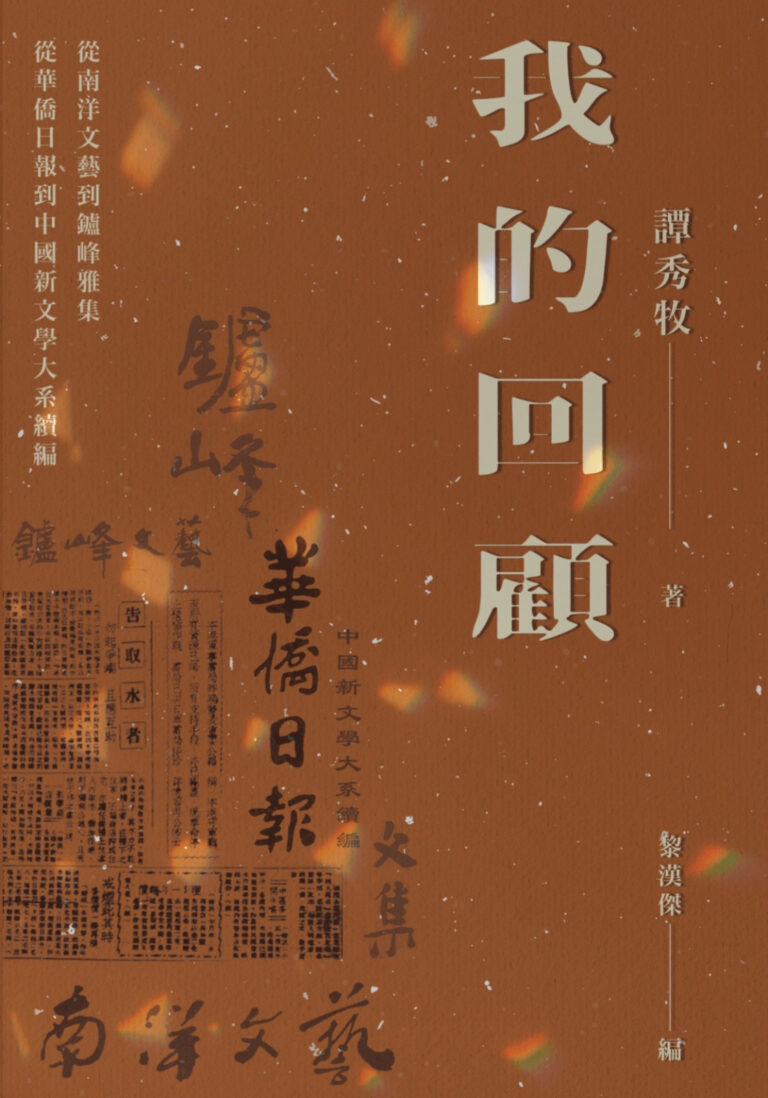編按:作者探討近年以廣州為背景的文學作品,透過細讀林棹、葛亮、魏微等作家的小說創作,分析其如何通過多元敘事手法,描繪廣州的城市風貌,揭示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大灣區城市精神。
近年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深入推進,「廣州敘事」悄然勃興,期間更是誕生了一批題材豐富、風格多樣的「廣州城市題材小說」,如林棹的《潮汐圖》、葛亮的《燕食記》、魏微的《煙霞裏》、宥予的《撞空》、索耳的《細叔魷魚輝》、伍華星的《入刀山》等。這批作品有別於簡單的城市地理志,它們憑藉多元的敘述形式和嶄新的文學觀,勾繪出廣州乃至整個大灣區城市歷史的獨特風貌,為當代漢語敘事注入了新鮮活力。
此處所謂「廣州城市題材小說」,指以廣州為背景、表現廣州歷史文化、社會生活及城市變遷等方面的小說創作,這類小說通常會深入挖掘廣州地理環境、方言習俗、歷史遺蹟、經濟發展、社會問題等,呈現廣州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特徵,經典作品有黃谷柳的《蝦球傳》(一九四七—一九四八)、歐陽山的《三家巷》(一九五九)、章以武的《雅馬哈魚檔》(一九八三)等。與既往的同類型題材不同,近年來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無論在敘述形式、人物塑造,還是對城市風貌的描寫上都有了新的變化。
長篇小說方面,林棹的《潮汐圖》(二○二一年)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巧妙融合粵語方言,塑造了一隻雌性巨蛙在十九世紀的廣州、澳門和英國的奇幻旅程。這部小說借畫師馮喜之口,對廣州城市風貌做了細緻描摹,更彰顯出一種博物學視野下的城市浮世繪:馮喜成名後在廣州靖遠街開畫肆(這條街坐落在番鬼、洋人、外江佬、廣府人混居的十三行一帶),他受博物學家H之邀為巨蛙製作博物畫,並教畫肆的夥計們認博物畫中的生靈(五彩蝶蛹、縫葉蟻大巢、萬物標本等),也教巨蛙識字(漢字、阿拉伯數字、羅馬數字)。馮喜眼中的世界,正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清代廣州,寰宇、世界、四海、萬國等名詞在此並非虛設,而指向東方與西方相遇、傳統和現代交融的歷史時刻,指向「天朝上國」(天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前夜。在這個時空中,不同的宇宙觀、知識系統碰撞出火花,博物學和博物水彩畫,即是一個縮影。
與之相對,葛亮則以「歷史小說」為方法,其《燕食記》(二○二一年)由榮貽生、陳五舉師徒二人的經歷鈎沉故事,空間上起於嶺南,終於粵港,時間上由辛亥革命至陳炯明治粵到當下約百年間。葛亮由此摸索到一條切近灣區地域文化和精神症候的取徑,這番努力在近期的「匠人系列」(如以香港髮廊為線索書寫世情變遷的《飛髮》)和《燕食記》這部全景式敘寫廣式茶樓興衰史的長篇裏開花結果。《飛髮》結尾,代表香港街坊精神的粵式「飛髮」師傅翟玉成與代表海派理髮的莊師傅的和解(莊師傅在病房為彌留的翟玉成理髮),象徵江湖道義,也寓意海派與粵港文化融合的可能——其中,翟玉成與鄭好彩夫妻相濡以沫的情節演變為《燕食記》裏陳五舉與戴鳳行的恩愛相助,讀來感人至深。可以說,葛亮對情義、道義的書寫儼然昇華為一種小說詩學。
多維筆觸刻畫廣州風貌
無獨有偶,作為「改開年代」的同時代人,魏微的寫作總是和時代的幽微變遷「同輻共輳」,這尤其體現在這部以「編年體」形式寫就的《煙霞裏》(小說最初在《收穫》刊發時擬命名為《一個人的編年史》)。小說大開大闔,從田莊的出生(一九七○年)一直寫到其猝然逝世(二○一一年),空間上遍及田莊生活過的李莊、清浦、江城和廣州,對田莊從村莊(李莊)到縣城(清浦、江城)再到城市(廣州)的人生軌跡做了一次巡禮和細描。其中對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圳和廣州的書寫尤其精彩,生動還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珠三角都市風貌,小說也借此將田莊個人的生活和國家社會做了巧妙「對接」,使二者「同呼吸、共命運」。
宥予的《撞空》(二○二三年)和我們尋常所見的長篇相距甚遠,它拒斥家族敘事,亦非成長小說,不依靠核心事件與衝突矛盾推動情節,更不以塑造人物形象為目標。從形式上看,它就像主人公何小河的一份「廣漂」生活日誌,以第一人稱視角,細膩描繪了其工作、生活瑣事與心路歷程,真實再現了無數外來者在廣州這座大都市中的生存狀態與情感體驗。尤其富有匠心的片段是小說的「第二部」,它以何小河對前女友陳小港的追憶開篇,繼而切入蘇鐵對彭冬傘的跟蹤過程。何小河為了揭開困惑(陳小港為何出現在筆記本裏?)決定還原蘇鐵的跟蹤路線。他行走在廣州城裏,海珠橋、小港路、草房圍……商舖、招牌、便利店、食肆、居民樓,街道的面貌、生活其中的人,南方城市的潮濕氣候、雨、雲、珠江和語言等,被何小河的目光一一掃描,凝固為紙上風景;蒲荔子的長篇新作《虛榮廣場》(二○二四年)則將目光對準二十一世紀初廣州的作品,其筆下的東山口、楊箕村、廣州火車站等地理位置、城市空間,散發着獨特的時代「光暈」(aura)。在描繪人物情感和心靈的同時,這部小說對廣州城市生活的複雜肌理做了深度透視,它通過敘述層面的「回顧視角」、對「成長小說」模式的擬仿,以及獨特的小說語法,寫出了人物複雜的情感結構,實現了對「文學廣州」的虛構與再造。此外,張欣的《如風似璧》(二○二四)以文學之筆重塑了「民國廣州」的城市形象,為廣州城市文學豎立起一座重要里程碑。
在中短篇小說方面,陳崇正的《開門》(二○二一年)通過「援非」醫生、抗疫志願者和門鎖修理工在封閉空間的相遇,構建了講述廣州故事和中國故事的敘事藍本;索耳的《細叔魷魚輝》(二○二三年)通過描繪上世紀九十年代廣漂青年「魷魚輝」在歌舞廳反串梅艷芳謀生的經歷,展現了一幅鮮活的廣州市民生活圖景。這部中篇小說從一九九三年寫起,橫穿二○○三年,被譽為「香港的女兒」的梅艷芳支撐着細叔從青年走向中年。這段精神成長史恰與廣州在「漫長的九十年代」的城市史和社會史發展同輻共輳。「魷魚輝」這一形象便是九十年代特定的「文學產物」,它糅合兩個原型(在廣州宵夜檔反串梅艷芳而出名的市井明星「炒螺明」以及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憑藉一支老舊紅色風筒闖蕩廣州燒烤江湖的「風筒輝」),如此鮮明動人,是近年來書寫粵地粵人的文學典型;與之可形成對照的,是同樣觀照九十年代省城(廣州)的中篇小說《入刀山》(二○二四):主人公進山探視入院多年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原本只為交送阿嫲去世後留給姐弟二人的微薄遺產,不料自己成為嚮導,帶領三個病人出逃下山(「出山」)。作者伍華星有意避開具體的時間標識,但小說裏啟用的大量粵方言和細節無不在提醒讀者:「我」與從福祉院逃出來的「阿弟」(「我」同父異母的姐姐)、波鞋哥和笑面人遊蕩之地,即是九十年代工廠林立、高速發展的廣州。
文學視角折射灣區精神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最具活力和潛力的區域之一,其城市文學呈現出獨特的風貌與魅力。而廣州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更是在當代城市文學中佔據着重要地位。從《潮汐圖》到《燕食記》,從《煙霞裏》到《撞空》,這些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的創作,既是對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是對全球化語境下城市發展的深刻反思。它們通過方言的創造性轉化、對城市空間的細膩描寫以及對人物命運的深入刻畫,呈現大灣區城市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交融和碰撞。在此意義上,「廣州城市題材小說」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更成為大灣區城市精神的生動寫照。
(作者為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廣東省作家協會簽約文學評論家,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雲山青年學者。)
爺爺的槍 ●王 溱
頂樓的房間租金自然便宜些。誰也不願爬那嘎吱作響的木樓梯,尤其是夜歸的時候,每踏一步都能聽見樓梯不滿的咒罵,樓道壁布滿冷峻的眼睛。她安慰自己說高點好,高點視野更廣闊,方便看日落,或者看日出,儘管這棟公寓也就五層,還不夠格關心太陽的行蹤。
「站得高,才能望得遠」——這是爺爺說的。
「居高臨下方可掌控敵情」——還是爺爺說的。
爺爺說的,她信。小時候她住碉樓,爺爺會把槍掛在碉樓最高一層的靠牆處,以便有什麼情況可以快速取下,槍口從牆上的小孔伸出瞄準來意不善的入侵者。她至今還記得木槍托在月光下泛出若有若無的光,那是被人常年摩挲出來的包漿。她也喜歡撫摸那槍托,滑滑的,涼涼的,有時還會把臉貼上去。童年因為這桿槍的存在而充滿安全感,即便自始至終她都沒見這桿槍響過,一回都沒有。據說爺爺的爺爺一槍沒開過就成了遠近聞名的神槍手。據說的,據爺爺說。
城裏沒有碉樓。這破公寓哪裏比得上碉樓?但她還是走到窗前學爺爺居高臨下瞪大雙眼巡視。遠處喧嘩的街市和近處稀落的路燈盡收眼底,她卻怎麼也摸不清「入侵者」的底細。「入侵者」不是人,是光。光影狡猾且變化多端,一下是圓形的,如手電筒所照,像極了一伙城市獵人在四處搜尋刺激;一下又雪花狀閃爍,如同用手機翻拍的黑白無聲電影,極有可能下一幕就是數不清的凌亂腳步,某隻鞋上還沾着嘔吐物;更放肆些的影子會靠近她,幾乎是緊貼着她眼皮底下晃,如醉漢搖晃的虛影,避無可避。
她忍住篩豆般顫抖的身體,假裝爺爺的槍此刻就在自己手裏,把槍口伸出去,瞄準。該朝哪兒瞄準呢?光影沒有形狀,總在她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又從她意想不到的地方消失。與其說像鬼魅,不如說像來自另一維度的怪物,身手敏捷且能隨意變幻,大能填滿整間屋子,小能擠進她手指上細狹的傷口。
胡亂瞄了一會兒,她的身體顫抖得更厲害了。這樣的「敵人」不像碉樓外的入侵者那樣由遠至近一步步靠近,即便手上真有槍,又能怎樣?
更何況,她沒槍。
記憶中的那桿槍隨着爺爺的離世不知所蹤。
喪訊是昨天阿爸打電話告訴她的,輕描淡寫。沒別的意思,就是告訴她不必急巴巴趕回來,該辦的都在辦了,早點入土為安,讓她安心留在城裏上班不必來回折騰。她自然不會聽,心裏悄悄琢磨怎樣跟老闆娘請假成功率更高。跟阿爸有一搭沒一搭聊了一會兒,她終於忍不住問起爺爺那桿槍的事,阿爸愕然,說家裏哪來的槍。她不甘心,給阿爸描述着槍的模樣,還有掛的位置,阿爸打斷她的話一口咬定就是沒有槍,說那是老黃曆的事兒了,家裏早就沒有槍。
沒有槍?
阿爸說得很篤定,沒有槍。
難怪眼前這些怪物如此肆無忌憚!她坐下,它就在牆上與她對峙,目光有些不滿,甚至帶着嫌棄,讓她想起今天開口請假時老闆娘看她的眼神;她站起時,它就往她背後跑,速度很快,總能在她回頭的那一瞬間消失不見,讓她心裏空落落完全沒底;浴室吊着的燈泡也被它收買了,一直搖晃,一閃一閃,隱約還帶着粗壯的喘氣聲。若怪物張大嘴把她一口吞了倒安寧,它偏不,一遍遍強迫她反芻今晚不堪的經歷。
今兒回家確實晚。她答應老闆娘把未來幾天的工作都做了才得以順利請假。午飯啃了包餅乾,晚飯也沒工夫吃,滿腦子都是電腦裏的數據,路走得踉踉蹌蹌,意識跟不上腳步。大意了,真的大意了,她竟忘了避開死角,避開陰仄的小巷。
那一群醉漢就在轉角處,動靜是有的,她竟半點沒有提前發現,待轉身欲往回走時已被人拉住,呼啦被圍在了中間。
她低聲求饒,顫抖的聲音瞬間被醉漢們肆無忌憚的笑淹沒。她便大聲呼救,更大聲的,是不知誰手中的酒瓶「啪啦」碎一地的聲音。
昏黃的街燈根本指望不上,它們只會把醉漢的身影與破碎的月光混在一起搖晃,地上的影子雜亂無章,空氣中瀰漫着嘔吐物的酸味。她下意識雙手抱胸往地上蹲,被一隻黏糊糊的大手硬拉起來,掙扎中她的手被什麼劃了一下,也不知流血沒,鑽心般地疼。
「住手!」
「放開那個女孩!」
「我報警啦!」
「還不快滾?!」
不遠處傳來響亮的幾聲喝。有路人經過,人數還不少。醉漢們沒有得逞。謝天謝地。
該死的光影們卻得逞了,尾隨她回了公寓。她好累,踏上木樓梯的步伐如同出殯般沉重,死一般寂靜的房間裏彷彿有哀樂奏響。記憶被凌亂的腳和交錯的身影攪得支離破碎,她蜷縮在床上,憶不起任何一張醉漢的臉,甚至搞不清那些身影的具體數量,如同一隻忘記弓長什麼樣的驚弓之鳥,獨自在這小小的房間裏瑟瑟發抖。
她決定開着燈睡,大大小小開了近十盞燈。足夠多的光源就能稀釋那些可怕的光影,這是無影燈的原理。方法沒問題,但這破公寓老舊的電路出了問題,才開一會兒就跳閘了。

(資料圖片)
啪!一片漆黑。
所幸窗外還掛着一輪不甚圓的明月,勉強把滿室漆黑變成稀釋過的淺黑。她揉着眼睛好讓眼睛快點適應,揉着揉着突然瞪大了雙眼。
槍!一桿槍!
餐桌有個長長的影子清晰可見,形狀像極了爺爺那桿槍!
她循着月光來的方向找,很快在窗台上找到了這桿「槍」的出處——一塊從手指上扯下來的創可貼。創可貼是今晚救了她的那幫人裏面一個可愛的圓臉女孩給她貼上的。女孩很細心,先拿純淨水洗傷口,用嘴吹乾,這才小心翼翼給她貼上,離開前還不忘輕輕摸摸她的臉,給她安慰。洗澡時創可貼打濕了,她便扯下來隨手放在窗台上,月光大概是受了誰的囑託,硬是把影子拉成了槍的形狀。
「怪物」早已逃得無影無蹤。她顫抖着伸出手去摸那桿「槍」,沒錯,滑滑的,涼涼的,忍不住把臉貼了上去。
「爺爺,我就知道你不會丟下我不管的……
憋了一晚的她終於大聲哭出來,哭得聲嘶力竭,猶如靈堂前的孝女。
(作者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長篇小說《嶺南偶遇》、《同一片海》、《第一縷光》及短篇小說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