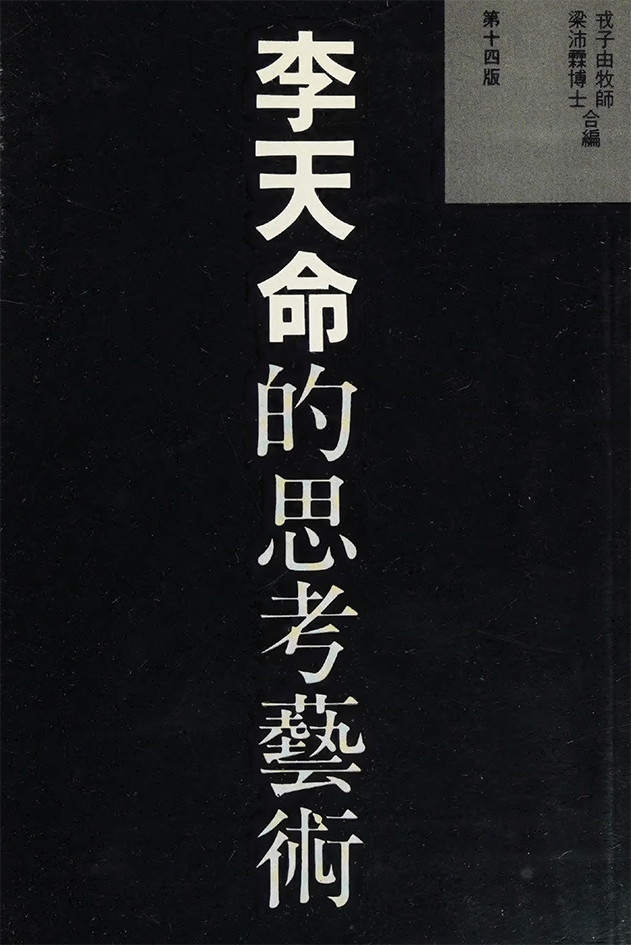鄰居的樹 ●胡燕青
在悉尼兒子家,鄰居的老樹是鄰居的痛症,卻是我的朋友。每一年到此地探訪兒子,總看見此樹越長越粗壯,佔去鄰居大片土地。澳洲的平房是連地買的(有地才讓價錢夠貴),買房子當然也得買下這樹。
此樹很大,樹冠下的地足以建一個四十人教室。可是,這裏沒有教室,只有幾個逐漸長高的小朋友。政府說這樹是先存於房子的大自然生物,不能砍。這麼一來,「祖母廂房」建不了,加個簷蓬也不容易。從用家的角度看,這真有點可惜。但從樹和樹的友人如鳥和蟲子、甚至樹腳下泥裏的微生物的角度看,這是不作他想的美麗家園。
我不知道樹的品種,只知道樹很健康,樹幹極粗大,樹枝疏密有致而且強壯圓潤、樹皮發亮,樹葉均勻分布,而且葉葉新鮮,每一細節都顯出樹生長得極好,即使斜着長高,依然穩固平衡。一群大鳥住在上面,代代繁衍,就好像我們寄居於地球。只見它的枝條高低起伏,猶如江山布置,各為風景,各成文化,真是陰陽割昏曉;估計高枝日暖如赤道、夜寒為極地;低處則陰涼濕潤,適合不同的鳥棲息活動,分頭經營自己的故鄉。從鳥蛋開始,他們孵化、待哺、成長、飛行,經歷美麗的南半球的日出和日落,然後回到樹裏去,每一天變老,等一天離開。
我們仰頭思考,卻無法進入他們的童年、愛情和生死。我們能做的,只是一個決定。把樹斬了多建一個廂房?讓樹留住容納一個世界?一時間,我竟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眷戀一個香港的小單位,和單位裏剛上小學的孩子。而單位當然可以是一個廂房,或者一個鳥巢。和樹相見多年,我見他越來越大,他見我越來越老。有一天我將再無力乘長程飛機到悉尼來,而樹自當繼續保護着這一群鳥。這友情將超過我們自己的生命。於是我為這一片相識的青綠命名:鄰居的樹。
一個下午太長,滄海桑田太短。人生的圖釘曾把我們固定在彼此的身邊,為彼此的小風景;這一切將飄蕩於記憶的大海,為海洋不至於單調。
(作者為香港作家。)
流年憶舊——吃食堂 ●張 欣
我年輕的時候在基層部隊醫院工作,當時的醫院工作人員有兩個食堂,一個是幹部灶,還有一個是戰士灶,兩邊的菜金補助不同,當然是幹部灶高,戰士灶又稱大灶,菜金低,許多基層部隊的大灶早餐也是大米飯配鹹菜,因為沒錢買麵粉而且戰士都是毛頭小夥,一頓吃七八個饅頭不在話下,伙食費就不夠吃了。
當時我已經提幹,所以吃幹部灶。說來奇怪,明明我們幹部灶這邊的菜金高,但是伙食卻不如戰士灶,由於兩個食堂挨的很近,大家出來進去的有時也會打飯到宿舍,發現戰士灶應季的新鮮蔬菜特別多,還有紅燒排骨、獅子頭啥的,我們幹部灶的炒菜裏難得見到肉,豆芽炒肉那就全豆芽,沙葛炒肉那就全沙葛,實在叫人難以下嚥啊。
一問,才知道戰士灶雖然菜金低,但是戰士們年輕、有朝氣,尤其女兵多還會過日子,召集大家一起去撿柴(樹枝、廢木頭啥的),當年的大鍋飯大鍋菜都是燒柴的,撿柴可以省菜金啊;他們還自己開荒種菜(基層醫院都是在山旮旯裏有的是地),澆水施肥長勢喜人;同時炊事班全體都是戰士,他們還自己養豬,你說那伙食能不好嗎?
反觀我們幹部灶就一司務長騎個二八寸的自行車去農貿市場買菜,如果司務長一不精明二不貪污(通常貪污的司務長單位伙食好)買的菜簡直讓人一言難盡,不是過季菜就是又老又糠,還有幹部灶炒菜的大師傅請的都是河南人屬部隊職工,手藝方面主要是會做麵食、饅頭、包子、花卷啥的,炒菜如果食材不行也難炒出什麼花來,說白了就是不好吃。
後來醫院後勤科的負責人也看着戰士灶眼熱了,說合灶合灶,一個醫院搞那麼多食堂幹嘛,心裏盤算着,幹部灶菜金高戰士佔便宜,但是戰士們勤快對於伙食有幫補兩頭都不吃虧。伙食肯定會比從前好。
結果並不是這麼回事,兩個食堂合併以後伙食更差了,為什麼呢,因為戰士們一看增加了那麼多人,怎麼撿柴種菜養豬都是供不應求就乾脆躺平什麼都不幹了,那他們本來菜金就少,合灶就等於佔了幹部灶的便宜何樂不為。
隔了一段時間,兩個灶又分開了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我那時候就知道人的本性都是趨利避害的,容易眼紅別人但其實又很難佔到別人的便宜,所以對於趨之若鶩的東西常常抱以警惕。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薛憶溈的「小眼睛」與其文學內觀 ●伍東林
薛憶溈的《小眼睛的小學生》遠非一部簡單的童年回憶錄。在其看似個人化的敘事之下,湧動着的是一部以精微筆觸重構歷史、以內省姿態勘探心靈的作品。它既是作家對其文學原點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清晰地映照出他作為一位「深圳作家」所特有的冷峻、敏感與跨地域的文學氣質。
小說的標題「小眼睛」本身就是一個絕佳的文學隱喻。它既指代一種生理特徵,更象徵着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不是宏大、全景式的俯瞰,而是聚焦、內斂甚至略帶偏執的凝視。薛憶溈正是通過這雙「小眼睛」,避開了歷史敘事的俗套,將波瀾壯闊的「大革命的大時代」溶解於一個敏感兒童的日常感知之中:入學年齡的困擾、寧鄉「留學」的惶惑、樣板戲台詞的語言魅力、對死亡與追悼會的最初驚懼……時代的風暴在孩童的視角中被折射成無數碎片,它們不再僅僅是政治符號,而是與個體的飢餓、羞恥、好奇與溫情緊密交織的生命體驗。這種「以小見大」的敘事策略,賦予了歷史以可觸摸的肌理與令人信服的毛邊。
薛憶溈的語言以其精確和冷靜著稱,他書寫苦難與荒誕,卻極少宣泄情緒,而是以一種近乎解剖學般的耐心,將個人與家族的際遇娓娓道來。外婆對「雙眼皮」的執念,交織着遺傳的遺憾與時代的審美焦慮;父親在「幹校」的境遇,通過「一大勺豬油」的尷尬細節得以呈現。這種克制而飽含張力的敘述,使得文本的情感力量不是撲面而來,而是靜水深流,在讀者掩卷之後愈發深沉。這正是薛憶溈文學風格的核心:他相信細節本身的力量,信任語言自身的邏輯。
作為一位常被打上「深圳作家」標籤的寫作者,薛憶溈的文學之路與這座城市的特質有着隱秘的共鳴。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消解固着的本土,強調流動與重構。薛憶溈的寫作,同樣具有這種「離散」與「重構」的氣質。他從湖南到深圳,再走向更廣闊的國際文壇,其筆下的人物與故事,往往也處在一種「在別處」的狀態。《小眼睛的小學生》中那個不斷在長沙、寧鄉、「幹校」之間輾轉的男孩,其心靈早早就體驗了「生活在別處」的疏離感。這種源於個人經歷的「漂泊感」,使他能以一種抽離而又充滿同情的目光審視故鄉與歷史,從而獲得一種超越地域性的普遍意義。
從他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寫作至今,三十六年的文學歷程,是一條不斷向內深挖、向語言極限挑戰的窄路。《小眼睛的小學生》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文學礦脈的一次深度回溯。書中對語言本身的迷戀(如對地名、簡稱的思考),對敘事真實與虛構界限的探索,是他在《遺棄》、《白求恩的孩子們》等作品中更為極致的文學追求的延續。
總而言之,《小眼睛的小學生》是進入薛憶溈文學世界的一把鑰匙。它告訴我們,一位傑出的作家如何從最個人的記憶出發,通過卓越的文學技藝與深邃的內省精神,將一段特定歷史轉化為關於成長、創傷與救贖的永恆敘事。薛憶溈以其「小眼睛」的專注,為我們洞開了一個無比深邃而廣闊的人性世界。
(作者為《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創作園地】■
心形胸針、擊中 ●舒 非
心形胸針
輕巧一枚胸針
扣在胸口
三朵紫羅蘭,由兩片綠葉扶持
清楚記得購買自那間舖
維也納大街轉角處
傍晚下過雨
雨後天放晴
濕漉漉石板路斜斜往上
有家琳瑯小店
你站在櫥窗前
指着心形胸針
好靚
我進店就買下
嗯,就是這枚胸針
今天獲得女詩人青睞
擊中
她一下擊中他最柔軟部位
社會染缸混跡多年
天涯海角走遍
風浪裏打滾
什麼世面沒見過
有什麼人無接觸
權貴有之
富豪有之
學者有之
名家有之
美女更是數不過來
可是偏讓她擊中了心扉
他的心並不全是冰冷
也有柔軟一角
那一角跟文藝關聯
年輕時代留下的印記
尋常看不見
觸動心扉時
突然湧現
猶如神奇噴泉
水珠在陽光下鑽石般閃爍
(作者為香港詩人及作家,曾任香港三聯書店策劃編輯。)
天眼仰看天外天 ●周蜜蜜
晨曦初醒,群山的臂彎裏
盤旋石陣的棋盤
星座在銅欄上流轉
引我們攀登,攀向天風迴旋的埡口
在峰巒合攏的瞬間
巨瞳自天坑睜開
——四千四百五十塊光年
正鍛成銀鱗,向深空鋪展
懸空處,衣衫鼓蕩如帆
山嶽般寂靜的鋼索
正測量月光下螞蟻的觸角
把脈衝星的信箋,譯成電波
當雲幕拉開,湛藍傾注
整座鏡面浮升為時空之鑰
那些行走在三角鋒刃的檢修者
多像穿越維度的光點
後來在球幕幽暗的腹中
射電流淌成宇宙的耳語
回望處,銀輪在萬壑間
每塊鏡面都盛着明天天外天——
天外天——這大地舉向蒼穹的明鏡
盛滿人類全部的明天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香江娥眉洲之色 ●冷 月
乙巳年七月十九,好友寄來在大埔拍攝的風景照云:「娥眉洲,位處船灣淡水湖之東北,被列入印洲塘海岸公園,乃潛水勝地。」因美景太美,與連日的黃、紅、黑雨形成強烈對比,故記述之。
黃色的傾盆,
紅色的警報,
黑色的瀑布,
黃、紅、黑恍似蒼天的悲嚎——
因狂放之徒而怒吼,
為受苦難者而悲愴!
藍色的晴空,
白色的雲朵,
綠色的山嶺,
藍、白、綠構成一幅文藝復興——
天然繪製而無添加,
定名為娥眉洲油畫。
黃、紅、黑警報後,
有看得見的藍、白、綠油畫,
還有看不見的紅橙黃綠青藍紫的雲霞,
環繞護持着這貨真價實的東方之珠。
(作者為香港作家,著有《錯失的緣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