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五月二十日,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明清研究中心特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到校,以「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為題,縱論一九四五年至今,香港古典詩詞教學的源流嬗變。本文為演講精華。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明清研究中心特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老師,蒞臨中央大學文學二館,以「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為題,縱論一九四五年至今,香港古典詩詞教學的源流嬗變。是次演講,由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明清研究中心主任李宜學老師主持。
庠序起新風——詩詞寫作教學簡史
詩選與詞選,是現今大專院校中文系的常規課程,內容以古典詩詞選授、習作訓練為主。但詩詞課的由來,乃至詩詞教學的發展脈絡,可謂知之者甚少。陳老師指,談論詩歌創作的歷史固然悠久,自唐到明清,不乏詩法著作,惟論述流於技術範疇,較為零碎。直至民國時期,西學東傳,學者整理國故,詩詞也因去古未遠,熱衷者眾,不少談論詩詞作法的著作因而問世。兼之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學文學院召開文科課程會議,討論如何設計中文科課程,詩選、詞選課程由此濫觴。其中最早呼應北大的,當屬謝無量的《詩學指南》、《詞學指南》,流傳於坊間,屬於補充讀物。而院校內部,講授詩詞的老師,則各自撰有教材,如北京大學黃節的《詩學》、東南大學顧實的《詩法捷要》、大夏大學馮振的《七言絕句作法舉隅》,皆為課堂講義、教材。甚至喻守真的《唐詩三百首詳析》,如今仍見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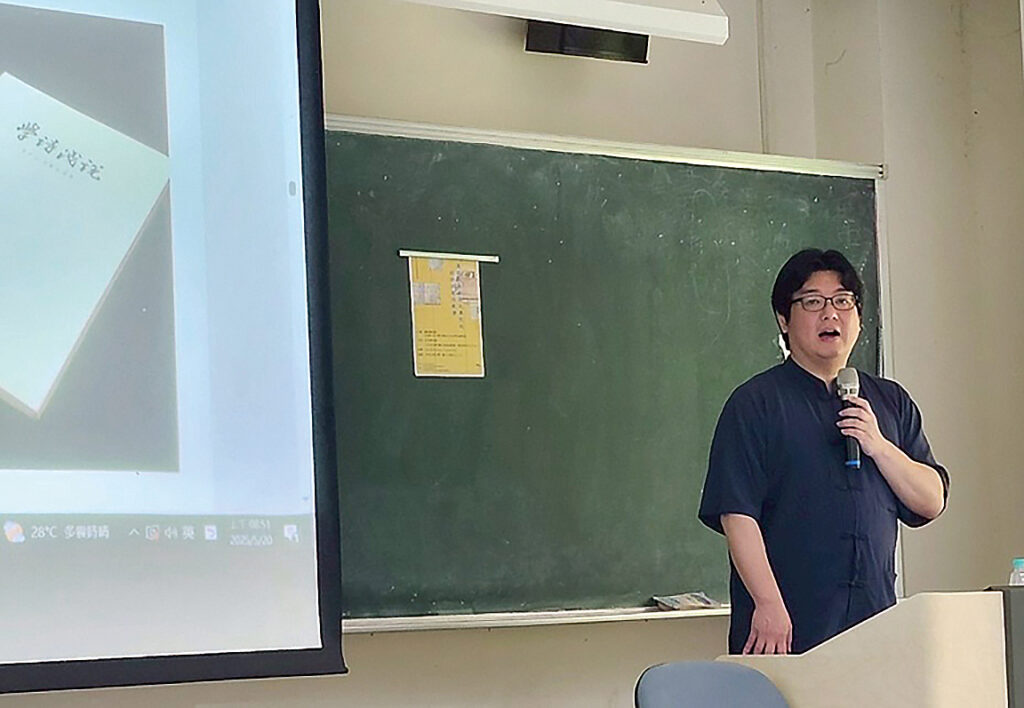
至於香港的詩詞教學,情況相對複雜。香港作為曾經的英殖民地,一度是醞釀革命的溫床。惟民國建立後,不少清朝遺老南下幽居,又香港開埠以來,商業發展帶動文化繁榮,受之影響,詩詞風氣仍熾。陳老師並提及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稱在民族主義、左派思潮影響下,英國統治者對時局不免憂虞,時任港督金文泰認為,要想保持香港治安,應加強中國的傳統教育,於是接納官紳建議,成立官立漢文中學,又延請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溫肅等進駐港大。不過,賴、區這類舊式文人雖然工詩,卻視之為小道而推重經史,因此這一時期的詩詞教育,仍處萌芽之初。
雖然賴、區等對詩詞興趣平平,但賴氏的學生李景康,頗能在詩詞教育方面有所建樹。他深知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決意將之納入政府管理體系。一九三○年代,李氏在漢文中學師範班之上,設置「詩選」科,復與葉佩瑜合纂《七言律法舉隅》,陳老師認為,這大概是香港古典詩新式教學的第一部教材。可惜的是,戰後漢文中學經歷改組,師範班取消,《七言律法舉隅》也無用武之地。但無庸置疑,這是戰前香港詩詞教學的一次重要嘗試。
金針度與人——戰後香港詩詞教育回顧
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不久兩岸分治,大批文人學者南下,他們與李景康同屬一代人,接力推動戰後香港的詩詞教育。其時本地人口驟增,幾所大專院校,如崇基、新亞、聯合等相繼成立,頗乏師資。諸如黃華表、易君左、鄭水心、曾克耑、熊潤桐、王韶生、涂公遂、鍾應梅等人,過去就讀或執教於內地大學,遂將新式教育觀念帶入香港,使詩選、詞選納入中文系必修。當然,各所院校對詩詞教育看法不一,如港大雖有劉百閔、羅忼烈等巨擘坐鎮,講學仍以作品賞析為主,詩選一向並非必修。而其他院校,則相對重視詩詞寫作。尤其七十年代後,香港中小學已不教授詩詞格律,大學生在缺乏基礎知識、訓練的情況下,旋即修讀詩、詞選,乃至做研究,進益有限,更不能彰顯中文系的專業。故大專院校講授詩詞創作,實肩負詩教傳承的重要責任。當年不少學生,至今依然緬懷先賢授課的情形,陳老師轉述其中一二,謂曾克耑執教新亞時,會布置課堂作業,即席創作,題目不乏詠飛機、電話等新題目。又,曾氏講課雖未必動聽,但他為學生改詩,認真仔細,頗能化腐朽為神奇。
當時香港院校詩詞教學選用的教材,大多為民國初年著作,除上文提及的幾部外,尚有鄒翰飛《作詩指導》、謝無量《詩詞入門》、張廷華與吳玉《學詩初步》、游國恩〈論寫作舊詩〉、瞿蛻園《學詩淺說》等。陳老師指,相較而言,居港學者專門撰寫新講義的情況則不多,其時或選用同門著作,或整理早年論詩文字。前者如曾克耑,以桐城門下,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為教材。後者如鄭水心,以一九五四年《新希望週刊》連載之〈詩鐘全貌〉作為任教聯合時的教材。陳老師認為,餘下堪稱完備,只有何敬羣於一九七四年編纂之《詩學纂要》,這是一九四五年以來,香港院校學者的第一部舊詩創作講義,內容以介紹詩歌淵源、聲調,與唐宋詩選讀為主。至於詞,因形式較詩複雜,其時教授入門著作亦多,如鄭水心於學海書樓主講之〈詞概:起源體裁及其作法〉,連載於《華僑日報》。而有「女中稼軒」之稱的陳璇珍,除在《華僑日報》發表文章,亦透過香港電台講詞,題為〈詞學漫談〉。另外,鍾應梅有《蕊園說詞》、何敬羣有《詞學纂要》,並以謝崧《詩詞指要》為此三十年間最後一部詩詞論著。

陳老師總結道,這時期香港詩詞教育,由南來文人主導,除在學院授課,他們亦廣泛結社,帶動民間創作風氣。此外,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重視時間效益的觀念深入人心,於是追求「速成」,成為香港詩詞教育有別於民國教學法的顯著特徵。最後,報刊、電台這類媒體,也對詩詞教育的推廣貢獻甚多,且這些材料,至今仍有待整理,頗具研究價值。
一九八○年以後,隨着老輩凋零,社團活動萎縮,新纂之詩詞作法著述亦見少有,僅以顧植槐《簡易詩法》較為知名。惟後生晚輩,仍以其他方式,宣揚古典詩詞創作風氣。陳老師提及其老師何文匯,多年主持全港公共圖書館詩詞比賽、新市鎮律詩、對聯比賽,向社會大眾積極推廣古典詩詞與粵音文化。何氏作為詩詞聲律研究學者,亦透過比賽,加深創作者對詩詞格律的重視。過去如李景康、何敬羣、鄭水心等先賢,對詩律拗救的認知或存在偏差,如今可謂「後出轉精」。至於陳老師自己,則從當年的參賽者,變為評審。雖然坊間或批評評審年年相同,入選作品甚少新意。但他直言,比賽並非純粹比拼才藝,尤其對於學生而言,透過入圍面試、即席對聯等互動,考驗作者,更具有深層的教育意義。如今,香港的詩詞傳統仍得以維持不輟,實應歸功於此。
(記錄整理者為璞社社員、本版特約記者。)
【學苑春秋‧師說師文】■ 痛

從痛到通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在籃球場上,不小心「篤魚蛋」了。所謂「十指痛歸心」身體上一點銳痛,便如針行於血,頃刻周身不舒服。甲骨文的「痛」字,如病榻之上汗珠滾落之形,一人臥於床,痛得出汗,細看真的繪聲繪形。痛楚襲來,何曾容你只割捨那小小一塊?
然而,解痛之道,竟也深藏於這古老的筆畫之中。在痛裏頭的「甬」字——它本是青銅巨鐘的懸柄。試想像那洪鐘被撞響之時,聲波就經此「甬」柄傳導,方能沛然震動,聲浪如潮,充盈整個空間。那是一種貫通無礙的力量。
奇妙之處在於,「通」字︰正是「辵」字以「行走」載着「甬」字而成。這便如同一艘輕靈的小舟,載着那根能傳導洪鐘巨響的柄,開始破浪前行。當「痛」的細針又要鑽進生活裏的某個缺口,我們需要的,正是按下那個內在的「甬」之按鈕,啟動那尋求通達流轉的航行——舒筋活絡,通則不痛了。
至於精神上的痛苦,像偶然不小心接下那甬柄,心魂之處那戚戚便瀰漫思緒,輾轉反側,有時更甚於肉體之苦楚。這時默想身心如一,同樣以「窮則變,變則通」的方法對應。海納百川才能讓心之小舟通行;甚至思考歷史貫通古今,從前人「痛苦」經驗中辨識路標。如活水,如行走,柳暗花明,不為一時一地之困境所滯。看開一點,以叩擊心靈的甬柄;繼續行走,才能驅動那載甬之舟的風。
如此看來︰痛是淤塞的泥沼,通則是載着鐘柄的小舟。按動那名為「甬」的按鈕,讓尋求通達的意志之舟啟程。無論身之淤塞,抑或心之鬱結,願以此「通」字為渡,輕舟雖時轉孤嶼,回看已過萬重山。

評鑑之痛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韓愈說,為師要做到傳道、授業、解惑,這是唐代人的想法。在學校裏,究竟誰是當家作主的,是老師,還是學生呢?在大學裏,課程完結時會有一份名為教學問卷的材料,讓學生填寫,以評鑑課程和老師的表現。從正面來看,教師在收到評鑑結果後,便可以據以改善課程設計,以及自身教學的表現。有不足者便加以改進,止於至善,莫過於此。
檢討大學教員的表現有三大方向,一為教學,二為研究,三為服務。研究可以量化,服務也有清楚的指引。教學的依據是什麼呢?那便是教學問卷裏的兩道問題,一是對課程內容的滿意程度,二是對任課老師的滿意程度。
可以先撇開課程的滿意程度,畢竟這是針對事而不針對人。學生上課,抒發對課程設計、教學內容是否滿意的感受,十分合適,也無可厚非。但對任課老師的滿意程度,便顯然是針對人而不是針對事了!
設計好課程內容,在教學時認真準備,教學時因材施教,在「課程內容」已經可以全面覆蓋了。老師本人要令到學生滿意,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那麼學生便是教師的老闆了!
於是,老師都不敢斥責學生。早上八點半的課堂,到來的學生往往未及半數,然後在往後的一小時裏,學生魚貫而至,好不熱鬧。按常理,面對如斯場景,老師當予以警告之詞。可惜的是,教學問卷還在學生手上,那道「對任課老師的滿意程度」的問題又顯然是對人不對事的,如此困境之下,絕大部分教師也只能忍氣吞聲,無可奈何。
多年前有一位台灣學者來訪,系裏安排了在我的八點半課堂讓他做演講。我心裏想,學生如潮水般前來,多麼失禮,也敗壞了香港的名聲。心生一計,求學說白了也只是求分數,於是安排了當天八點半來個小測,在九點才邀請該學者蒞臨。結果當然是美滿的,學生精神抖擻,準時入座,台灣學者深感香港學風醇正,學生準時上課,提問踴躍(當然也是事前已作安排的),甚感欣慰;卻不知他們只是為了應考而來。
視學生為顧客,或以之為老闆,冠冕堂皇來說,名之為「學生為本」。在教學之時,究竟是老師要為學生的好,然後制訂教學內容,還是跟學生詳加商議,從而調整教學方針。何者為是,言人人殊。老師不必高高在上,但學生也要尊師重道,免卻了為師的痛苦,學術才可得以承傳下去。

隱隱痛
●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醫生時常要病人形容痛感,若描述含糊不清,更會要求病人以程度區分,十分為滿分。這方法非常務實,讓抽象、難以比擬的主觀感受,鑲嵌在一把有刻度的量度尺上:十分要即時處理,七分就持觀望態度,兩分嗎?你就多等一會,外面還有一群六分的叫苦連天。還有就是責任問題,痛的程度由病人打分,醫生大可以安坐電腦椅,把頭枕在雙手上,指自己只是對症下藥,原來你能這麼忍受痛楚?我真是佩服!
但一分的痛感,是否就不用即時處理,讓時間靜靜治理就好?若痛感一直蟄伏體內深處,偶爾爬出來刺一下,開懷大笑時又刺一下,提醒宿主,你是不應過於快樂。
去年送別一群畢業班同學,他們全修讀商科,語文一環尤其羸弱,我拉牛上樹,才勉強讓他們完成一篇符合字數要求的作文。然而曾收到學生T一篇作文,真人真事,讓我動容,每每想起也隱隱作痛。題目是二○二三年文憑試題目「一次令我百感交集的聚餐」。
內容憶述中四最後一天上課天,某同學宣布往海外升學,而身為班主任的我,允許他們到我新居天台燒烤,作為歡送。那天我們相約坑口,同學逐一現身在地鐵站,全員到齊後,我才道出其中一位同學需要居家隔離,T心裏已覺遺憾。買好食材到埗,我請他們先到室內休息,T自告奮勇,率先到天台張羅,安頓好再請我們上去。學生來來去去,開門關門。我們聊天、玩桌遊,沒有人發現T正默默烤肉,放在一邊讓我們隨時享用。文章裏有一支節,是他某次抬頭,竟發現天台剩下自己,所有人都不知所終。
活動後我送他們到巴士站,著學生回去後在群組「報平安」。學生魚貫上車,T坐在最後一排,看着同學一個接一個離座,直至將要退學那位也站起,彼此交換一句「下次見。」便下了車。餘下就只有自己。T回到家沒有在群組回覆,而是私訊班主任報到。我這才發現他的心意——希望聚會永不結束。
無數微小的痛充斥文章,沒有直接抒情,因為快樂下卑微的痛,已布滿全身,隱隱作痛。畢業那天,學生說起未來,T說:「我想往後再沒有這三年過得如此快樂。」又一次無聲的鼻酸。只是那時他不知道,留學他方的同學總在假期回來,而我千叮萬囑T要在公開試重寫這題材,他突然亂寫一通,最後中文不合格收場,才讓為師感受到十級痛楚。

古早味的走馬燈
●香港中文大學 吳琪琪
家鄉的古早味是舌尖上的走馬燈,轉一圈就少一味。那一年踏進城隍廟,海風裹着油香撲面而來。
糖房街的甜味是有形狀的。花生湯老闆舀起濃稠的琥珀,湯汁緩慢滑落,沖進土雞蛋裏瞬間開出蛋花。碗底的芋塊吸飽甜汁,柔軟得像年輕時的心思,輕輕一擠便滲出糖水。
轉角那家芋圓舖,老師傅刨芋絲的手勢快又準,湯鍋掀開時,白霧裏浮着肉餡的輪廓,剪開的芋包淌出白色的骨湯。花生糖碎落在上面,像一場金色的雪。
城隍廟的香火是另一種味道。朱漆供桌上的三牲五果堆成小山,金紙燃燒的青煙裏飄着檀香枝的清香。穿碎花襖的阿嬤拜得虔誠,髮髻上的銀簪隨着叩首輕輕搖晃,落在橘子皮上,微弱卻耀眼。
這些味道都在消失。就像老街騎樓的彩瓷一片片剝落,像魚販鐵盆裏銀光黯淡的帶魚,像手工潤餅皮上的焦斑,再難復刻的火候。
我站在城隍街的廢墟前,鋼筋刺穿騎樓的腹部,挖掘機的轟鳴蓋過了記憶裏的叫賣聲。回想去年此時,花生糖的甜香還纏繞在糖房街的晨霧裏。
原來,所謂古早,不過是時光在心頭尖上輕咬了一口,留下又甜又痛的牙印。

疼痛如礪,許生命如詩
●澳門培正中學 曲書頤
夜裏,小腿忽然抽筋了。
那是一種隱秘的痛,肌肉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攥住,緩緩絞緊,感覺像從骨頭深處滲出來,並順着筋脈蔓延,怎麼也甩不開那股鈍鈍的疼。大人們總笑着說:「是抽條呢,好事。」可沒人告訴我,長大原來是一件帶着隱痛的事。
青春的敏感,像一場漫長的陰雨天。照鏡子時,總覺得自己的臉不夠好看,身材不夠勻稱,說話不夠伶俐,舉止不夠從容。那種難堪,真像一把鈍刀磨着血肉,讓人坐立不安。
後來,疼痛褪去,身體定型,卻在皮膚上留下證據——生長紋。大腿外側、膝蓋內側,甚至是腰際,淡銀色的紋路像河流的分支,蜿蜒在皮膚上。它們不痛不癢,只是沉默地宣告這裏被猛烈地撐開,記錄了那些沉默的夜晚,以及無聲的痛。
直到我在社交媒體看到一個女孩。在意大利午後的海灘上,她穿著清涼,陽光吻過雙腿的銀色紋路,在地中海的碧波間閃閃發亮。我私信問她,她卻回覆我:「它們不是裂痕,是河流。以前總是遮遮掩掩,可它們正是我們成長的證明啊!」
我終於發現,原來真正的成長,不是擺脫所有疼痛,而是學會與傷痕共處;不是成為完美無缺的人,而是有勇氣面對那個不完美的自己。
生長紋,是歲月的勳章。它們證明我曾勇敢疼痛過,卻依然選擇如河水般肆意流淌,像大樹般昂揚生長,似詩歌般盼望遠方。它們讓我意識到:我只是我,我就是我,一個特別的我。

消散過後的痛
●顯理中學 丁加文
「痛」:部首為疒字部,也或許是由古人流傳下來,「痛」是難以承受的。「痛」是急性的、短暫間歇的、淺表的、熱灼的、開放發散的、尖銳的疼,我想人們討厭它,我也不例外。
由我有記憶以來,痛是身體帶出的警號。小時候頑皮得很,想像自己是什麼有特異功能的人,不顧身體的限制,總是挑戰身體的極限,嘗試告訴身體,誰才是主人。可換來的卻是在遊樂園不帶眼,猛烈地向前衝,撞倒欄杆、門牙離我而去、額頭起包的疼痛。我哭鬧着,但痛感並沒有離開我,我知道哭沒有用,我只是試圖引起同情,那刻起我知道——「痛」,是壞人。
長大了,也許是我知道自己沒有依靠,耐痛能力也高了。「社會大學」教會我太多,看清社會,看清人類後,領會的又是第二種「痛」。那怕是血流不止也好,我的神經似是再沒有知覺那樣,告訴我,警告我,我痛了。
那「痛」,不知何時起,一直纏繞着我至今,那是開放發散,侵蝕着我的痛。是吃多少止痛藥也止不住的,折磨得教人感到窒息的,每吸一口氣,那氧氣似是變成針一樣,蠶食着肺部的每一處。止不住的眼淚,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汪洋,是試圖哭訴着被這地打壓的「痛」。但可笑的是,大家也在這極度痛苦、極度瘋狂的地方如此痛苦地活着,為的是什麼,是為了一份能對得住父母的成績?是為了能活在這城的薪水?還是要證明自己的價值?我想不到,因為最可笑的是,我連幻想日後的一切都感到痛苦,我看不清未來,不敢去看,現實太過殘酷,我只是想着明天也感到害怕,還有什麼資格談論未來。
我想被人在意,可我卻總是把自己困住,我想自救,但現實給了我重重一擊,我不配。為何我活着是想着為誰,為何我努力過後卻失去自我,或許這就是人們所謂的「情緒病」。對的,我生病了,也許是吃抗生素也好不了的一場大病,我想着讓痛感一點點地喚醒我尚餘的一點感覺,好讓我知道自己還活着,我還能戰勝那「痛」。
但,謝謝那痛,迫切地使我在這地成長,學會更多,也許往好的去想,這「痛」保護着我,教我比他人更早看透我現時擁有的一切,教我去珍惜仍然願意和我走向未來的人,教我去努力感受快樂。

生長痛
●香港中文大學 胡珮嘉
男和女,到底有什麼分別呢。我常常想。六歲,穿上純白校服裙,媽媽柔軟的手編出馬尾,那都是校巴上的男同學頭上沒有的,他沒有裙,他穿著像煙囪似的,名為褲。所以,女生是長髮、男生是短髮;女生是裙子,男生是褲子,我決定要這樣分。
男和女,到底有什麼分別呢。我依然在想。十一歲,不知名的痛在滋生,從左邊的胸口開始蔓延,其後化為膨脹,用一把刀將胸口雕琢出弧度,再之後是骨盆,被雕刻的痛楚從上而下。最後,血初次從兩腿間流出,蜿蜒於大腿內側,如蛇一樣,緩緩而下,滴在瓷磚上,變成血紅色的花。
「每天都穿上這個就好了。」媽媽笑着。原本自由的部位,長出新的骨肉,我將她們放進鋼圈。「每月都用這個就好了。」媽媽從櫃子裏拿出一包,藏起所有的血紅,此後四十年,忍住每月定時收縮的痛,如常生活。於是,我的世界從此性別分明——每天都穿上這個就好了……每月都用這個就好了……某個器官每月在皮膚下扭動,疼痛,直到最深處……我尋找同類,與我共享疼痛的人。那裏會有幾百個我,再沒有鮮明的分別。或許,我可以習慣被束縛的胸脯,我可以忍受子宮的銳痛,然後在很久之後,我學會和所有不自由平靜共處,無視身體的疼痛,甚至去孕育。那時,我會是真正的大人。

永遠不能忘記的痛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郭妍心
「痛」是一種警報,如手觸碰到火的灼熱就是痛覺。心靈的痛更是劇烈的、把人絞裂的,我認為世界沒有永恆,痛苦卻像無底深淵。
前陣子我到訪梵高的展覽,看到了他的一生。從「夜晚露天咖啡座」的熱鬧溫暖、「星夜」的迷失癲狂,再到繪畫田園的恬靜溫柔,使我感受到那些掙扎、堅持和不被理解,是多麼深沉的痛苦。自責、絕望、孤單,最終都在「麥田群鴉」中解脫,梵高也悄然無聲地自我了結。
我自幼也經歷過各種痛苦,家庭破碎的痛、遭受背叛的痛、被拋棄的痛、懊悔自責的痛、不被理解的痛,還有麻木的痛。痛到極致是麻痺,身體如被電擊一般,劇痛會震碎所有知覺把人掏空,靈魂便墜落在沉寂深海。我猜想上帝發明痛的本意是保護人類,就像觸碰火時手會本能退縮。人類在面對承受不了的痛苦時,身體或心靈會啟動保護機制,例如選擇遺忘。
然而,某些痛是永遠無法忘記的,我們只能帶着它拼盡全力跛行。痛苦很多時候必須獨自面對,我想那就是一種成長的痛,是靈魂的年輪,記錄着每次成長的印記;是持刀的匠人,一刀刀剔去軟弱,鑿出靈魂稜角,使我們變得更加堅強獨立,更有經驗面對問題和保護自己。即使很痛很痛,也不要緊,請好好擁抱那個還很痛的你,對生命驚人的韌性,致最深的虔敬。

灰燼危花
●顯理中學 陳羨貽
廢墟上空飛絮着無名不安,暗沉氣壓彷彿下秒就壓在我們身上,你擺擺手,轉身離去,我蹲下身,從地上拾起泛黃的拍立得,內裏人影已模糊不清,隱約看到的,只是情緒。
晨光照下課室,我看着你手握白向日葵,說這是永恆的象徵,我歪了頭,目光從你的臉移到花蕊上,嘴角不自覺上揚回:「是嗎?我不知道呢。」畢業袍下擺在草地拖曳,心情也隨着被牽引,叫囂着疼痛,沒理由來的疼痛。
回過神來,你站在我眼前粲然笑問:「怎麼了?」我搖了搖頭示意沒事,你挽起我的手臂,微風拂過我的視線,你的聲音在風中拼湊,重寫,又隨着絲流而去,我點點頭——「咔嗒。」相機鍵輕敲在心弦上,似乎有些被縫上的傷口重新裂開,窺探着彼此,誓要探出個什麼來。
我攥着相紙,道不出什麼來只覺得悶得慌,我還是沒忍住那句早就在心底重複、疑惑、練習的——「我們還會再見嗎?」你一瞬頓住神情,片刻過後你莞然而笑,「這說的是什麼話?我只是畢業又不是離開了。」
不,你離開了。「當然會再見啊。」
對啊,這不是你說的嗎?那為什麼你現在這樣看着我?那為什麼我們的重逢會是這樣?困惑、不解、慍惱充斥着我的腦海但不得不看着眼前人,白裙黑袍飄逸對比,眼前霓虹光燈恍惚,與記憶重疊,卻不與回憶重合沉鬱。
如果那年秋天蝴蝶不在山谷流連,湖面上的枯葉沒有擱淺,我是否就能留住你,我的眷戀是不是就不會被流放?月光映着雙影模糊手上的焦點,你嘆息着撕下關係。
當意識到我們快要踏進人生十字路口時,必須直視離別和感受生命的傷痛。我在這片瀕死土壤上談論着荒唐的夢,最後只化作灰燼危花沉積在我的苦難。
我問一句作結:「會再見嗎?」你淡然說道:「不會,再也不會了。」

痛的無辜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陳煌森
失眠是我高中三年的底色,嚴重時一周的睡眠竟不足二十四小時。那時人是離心的軀殼,僅靠抽抽噎噎的痛覺栓住。痛的坦露或許僅需等待與調停;也或許,是對教育壓迫的自殘式反抗。傳統家庭擅長將痛楚翻譯為一種道德缺陷——彷彿失眠只是懶惰的變體,偏頭痛不過是畏難的藉口。我被迫承認我的神經在叛逃,我的血管裏流淌着懦夫的血。這種被迫的自我定罪,我發現自己成了一個詭異的容器,裏面總有一個批判者舉着「堅強」的火焚燒我的「軟弱」。每每肉體忍不住燙而顫抖時,腦海總要高喊「忍下去!」我忽然驚覺——我既是刑求者,也是囚徒。
每晚,我勢必要扮演熟睡的酒徒,欺騙明天的我有義務上學。然而寧靜的黑色總是被痛戳破,顯得格外清醒,我竟然追問了許多我庸俗一生不敢覺察的問題。為何學習必須是吞嚥而非品嘗?為何割下我自主性的血肉餵養集體的饕餮?諷刺的是,學校與父母十多年來的擠壓令我遠離書桌,而痛卻讓我愛上閱讀,像在荒漠中舔舐自己的傷口,嘗到自由的腥鹹。後來我問:痛在恐懼什麼?透過閱讀與思考,我開始反問:這份根植於我體內的痛,它自身又在恐懼什麼?恍然發現災難化思維原來就是意識裏潛藏着「考不上大學你就完了」這句話。
當我讀到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事物本身並不直接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我們對它們的看法來影響我們」後,我在某個凌晨忽然想通了:原來,痛本身也是無辜的。它並非敵人,而更像一個信使,忠實地傳達了那個被恐懼所扭曲的系統施加於我的一切。

不懂得游泳的魚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黃喧詠
生活中總是會經歷許多種痛,做功課被紙割傷的刺痛,跌倒時膝蓋擦傷的腫痛,胃痛時的絞痛……這些都是很常見的痛,只要忍一忍,等待它自然康復便好。可總有些痛不斷地圍繞着我,如影隨形的,消失一段時間後又出現,像是遊戲中死亡後看廣告復活的角色一般,殺也殺不死。
每當壓力來臨時,那種感覺彷彿就像魚跳出了魚缸,躺在地上喘不過氣一般,奮力掙扎卻又無能為力,那種無法呼吸的痛苦無處訴說,也無法解脫。這種痛苦是無法與日常中那些碰撞出來的痛比較的。
我曾問過大人們:「成長是如此痛苦難忍的嗎?」得到的回答卻只是「這算什麼!我吃過的苦比你痛多了……」人與人的痛苦可以比較嗎?是我過於軟弱了嗎?此刻的我,是那條不懂得游泳的魚,被一層一層的浪蓋過,在那湧動的水流中溺水。
路還有很長,我有點害怕疼痛的滋味,但是沒辦法,成長也許就是如抽筋拔骨般疼痛吧!直到某天,當我能在沒有水的地面上呼吸時,也許我已經堅強地長成可以隨意說出「這算什麼」的「大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