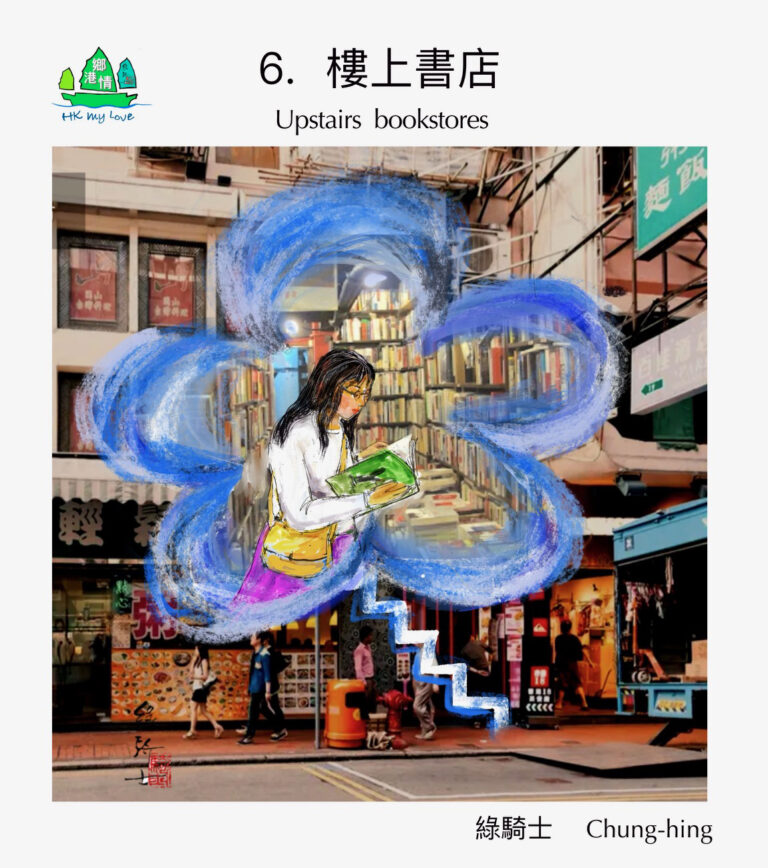編按:「這些年,這裏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越來越多的鷺鳥飛來天藍、水清、岸綠的星湖繁衍生息。」肇慶老城中的山水景致吸引各種鳥類。「『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句話講的不正是眼前的這個小鳥的新天堂嗎?」
長時間伏案工作,有時候偶然抬頭,看窗外的湖光山色,藍天白雲,成群結隊自由飛過的鷺鳥,會有種穿越時空看年輕時自己的感覺,儘管隨心所欲早已漸行漸遠,但還是覺得時光未老,尚能繼續前行。
在倍感疲憊的時候,這座山環水抱的城市,這座因端硯而聞名古稱端州的城市,這座山好水好湖好、硯端政端人端的城市,這座因宋徽宗認為會給他帶來喜慶而被命名為肇慶的古老城市,總會給你一個喘息的機會。於是,每周的一兩個下午下班時,會選擇沿着星湖邊那條綠樹成蔭生機盎然的堤路,慢慢的走回家。
肇慶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天空似乎觸手可及,水光瀲灧中,遠山近樹全倒影在湖中,清晰可見。「水似萬尺錦緞接遠天,岩如七星飛降落山前……」在浮動的光影和習習涼風中,一邊踽踽獨行,一邊輕聲哼着這首輕快的廣東第一首粵語流行曲,案牘之勞形瞬間煙消雲散。
湖中,狀如北斗七星排列的七座岩峰倒影於湖中與天光雲影融為一體,會讓走在湖邊的人有種徜徉天際的感覺,這不就是水天一色嗎?這不就是水清樹綠景美人悅嗎?湖上,七座岩峰陡如峭壁,壁上岩縫日積月累竟積攢出肥沃的土壤,長出了許多姿態各異生命力頑強的劍花與雞蛋花樹,形成蔚為壯觀的「峭壁森林」。湖下,湖水清澈見底,長滿隨波飄搖的長長水草,又儼然另外一片「水下森林」。竹筏劃過水面,驚起幾隻小水鴨,振翅而起。面對如此美景,少年時一個猛子扎進老家小河穿越搖曳水草追逐魚群與蝌蚪群的畫面驀地重現。天光水色之間,彷彿每一條飄動的水草,都是蔓延的童年記憶。
夕陽西下,遠處慢慢有無數的鷺鳥成群結隊飛過來。牠們時而低飛盤旋,時而在湖面覓食,時而在枝頭嬉戲。湖上幾個小島的茂密樹林上,全站滿了大大小小的鳥。
「朋友陳把手一拍,我們便看見一隻大鳥飛起來,接着又看見第二隻、第三隻。我們繼續拍掌。很快地這個樹林變得很熱鬧了。到處都是鳥聲,到處都是鳥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飛起來,有的在撲翅膀……我的眼睛真是應接不暇,看清楚這隻,又看漏了那隻,看見了那隻,第三隻又飛走了。」這不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著名作家巴金筆下的「小鳥天堂」嗎?
驀然驚覺,這些年,這裏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越來越多的鷺鳥飛來天藍、水清、岸綠的星湖繁衍生息。不經意之間,竟慢慢成了令人歎為觀止的「鷺鳥紛飛」、「萬鳥投林」的美景。忽然間覺得,「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句話講的不正是眼前的這個小鳥的新天堂嗎?
這一刻,不由想起生斯長於斯的古端州人,其實很早就有環保的意識。四百多年前的明萬曆年間,兩廣總督戴燿為保護七星岩不受破壞,便於湖對岸的石室岩洞外東壁刻下「澤梁無禁,岩石勿伐」八個石刻大字,意思是說這裏捕魚不加禁止,砍伐樹木,破壞山岩,決不允許。
「肇慶是一個能真正連接傳統和現實的地方……」走下東堤時,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老師來肇慶看端硯時說過的那番話猶在耳畔:「每一方好的端硯,都能讓人重識傳統文化的精微和榮光。我常想起當年被貶嶺南的蘇東坡曾寫信給黃庭堅說:『吾當往端溪,可為公購硯』,每次來肇慶,我也會給遠方的文友買一兩方端硯。硯石裏藏着那條珍貴的文化絲線,一直綿延至今……」
一隻落單的歸鳥張開翅膀,向湖中的小島疾飛。天就快黑了,我加快腳步,朝家的方向走去。
我心安處是我家,願每一隻生活在這裏的小鳥,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主席。)

老城印記 ●黎曉陽
一眉彎月悄悄探出雲影,像焦距捕捉到的影像,在朦朧的夜空中逐漸明亮、清晰,彷彿睡眼惺忪的美人舒開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
風,陶醉了。彷彿隨月光款款而來,穿過幽邃的羚羊峽,掠過蜿蜒而秀麗的西江,像精靈一般闖進這座古老的端州城,敲響了宋城牆內永明宮上簷鈴,鈴聲陣陣,猶如珠落銀盤,驚飛了瓦脊上的一行飛鳥。
端州,又名端城,隸屬廣東肇慶市管轄,至今有兩千多年歷史。開國元勳葉劍英元帥就曾賦詩:「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陽朔七堆山,堤邊添上絲絲柳,畫幅長留天地間。」盛讚肇慶星湖的秀美景色。
星湖,境如其名,星河之畔,湖光山色,如人間仙境。每至春季,十里湖堤,馥鬱芬芳,七彩紫荊爭相競放。一朵朵,一簇簇,掛滿枝頭。倘若空中俯瞰,蜿蜒的湖岸線宛如一條七彩飛花的紐帶,把山、湖、城、江,點綴得色彩斑斕。到了夏季,荷香瑟瑟,端州八景之一的「寶月台」荷花盛開。紅荷翠葉,宛如城中鑲嵌了一顆翡翠明珠。
我出生在端州的騎樓街,在那裏長到七歲。那時老城很小,一條東西走向的騎樓街貫穿着老城區。騎樓街有書店、藥房、麵館、打鐵舖、雜貨舖。除此以外,城內街巷縱橫,四通八達,大大小小的胡同像人體複雜的脈絡。如「米倉巷」、「擔水巷」、「五經里」、「草鞋街」、「立新街」、「水師營」,九曲十八彎的胡同幾乎每個名字背後都蘊含着一段歷史或故事。當然,胡同雖老,卻活像一個神采奕奕的老人,時刻充滿着人間「煙火」。
那時候,水電資源仍十分緊缺。每到傍晚,常有穿著背心或光着膀子的人群在「騎樓」下歇息乘涼,婦女多是坐着小板凳圍成一團,一邊搖着蒲扇,一邊借着路燈的光線做手上的活兒。更有甚者,乾脆把沙發搬到騎樓下南柯一夢……那年頭,老街朝氣蓬勃、樂也融融。「青壯年」有永遠忙不完的活,挑水、劈柴、買煤球,整天忙得不亦樂乎。小孩則是滿街滿巷地瘋跑,到了開飯的時候,大人會站在屋前,吆喝幾聲,然後某個角落總會冒出個影子來,屁顛屁顛地往這邊跑……
那時根本沒有現代的娛樂設施,可騎樓老街卻啥都是開心的玩意。哪怕是一根電杆、一條繩子、一個線圈、一個樹杈,都可能想像出創意十足的遊戲。總而言之,那時只有你想不到的,卻沒有做不到的。爬樹攀竹,游泳翻牆,甚至打反叉倒立走路,幾乎無所不能。
臨近春節,老街年味就更濃了。端州人一直有包「裹蒸」的習俗。除夕前夕,家家戶戶在老街壘起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土灶,晝夜通明,熊熊的灶火遍布城中的街頭巷尾,零落的鞭炮聲已經告訴了你,新春將至。
八十年代初,我隨父親返回廣州。臨行前的一天,我坐上父親的「二八大杠」(自行車)。鄰家謝姓女孩坐在車前架,我坐在車後架。那天她高興得手舞足蹈,不時把手伸到後面拉我的手,我則躲在父親身後扯她的衣角,她被逗得「格格」地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回憶裏,父親常常把她稱做「格格」。或許,那天真無邪的笑聲,從那一刻開始已經楔入父親的記憶裏。
那天,我第一次領略到被藍天白雲追逐的感覺,第一次感受到那種來自陌生而艷羨的目光。兩旁飛快倒退的房屋,路面像黏着輪子滾動起來,我們的情緒也跟隨着輪子飛轉起來。「格格」將身子前傾,展開她柔弱的臂膀,那頭平肩的秀髮像被風吹散的青煙,在風中起舞。
啊,她宛如一隻嗷嗷待哺的雛鳥,對世界充滿着無比的好奇和渴望。
望着那拉長而變形的影子,掠過斑駁的城垛,掠過深巷老宅中的院牆,忽然,我對省城那份熱熾的嚮往消失了,心頭莫名其妙地湧起一陣又一陣對老街的眷戀。
最終,我還是離開了這座城市。離別當天,「格格」站在送別的人群裏,一言不發。她眼神流露出無奈與傷感。當我踏上客輪的那一刻,她終於飛奔過來,湊在我的耳邊輕聲說,騎樓前的磚縫裏有一把鑰匙,哪天我回來了,可以用它打開東廂的小書房。
離開老街我就再也沒見過「格格」了。我曾在九十年代前回去過兩趟,找到她楔入磚縫裏的鑰匙。那時「格格」一家搬離老街已經好幾年了。記得推開那矮小的門扉,空氣中充斥着一股陳舊的黴氣,書架上掛着一把結他,書籍已經發黃了,被一塊繡着「日月」的大紅花布覆蓋着。
離開「倒數」的人群,循着璀璨的燈光穿過人流如織的騎樓街,我在尋找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騎樓。忽然,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撲面而來,我發現東廂的門頭上面寫着「易燈書店」,我的腦海馬上閃出了那塊大紅花布和結他……
(作者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駐村記》等。)
那年那月那座山 ●李羅斌
豆腐村的劉、黃兩家同日娶親,新郎官劉旺、黃柳是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好得不得了。
豆腐村以做豆腐出名,而尤以劉、黃兩家做得最好,方圓百里聞名。村前有座山,是進村的必經之路。傍晚,當兩支抬花轎迎親的隊伍在山裏相遇時,山上突然下起了雨,兩夥迎親隊伍放下花轎,躲進破廟裏歇腳避雨。在雨中,只是苦了一對新娘,礙於禮數和面子,在大紅花轎裏動彈不得。幸好,只是陣雨,很快就停了,兩夥人就又開始上路了。
混亂間,兩夥人把花轎給調錯了,劉旺的新娘抬進了黃柳的家,黃柳的新娘錯入了劉旺的屋。本來,新郎官在揭新娘的紅蓋頭時,就會發覺新娘弄錯了,然後趁着夜色把新娘悄悄換過來,彼此都沒損失,這個大笑話也就不會造成大錯。可是,劉旺和黃柳都是貪杯之人,大喜之日,更是喝個酩酊大醉,入洞房時熄了燈火只顧抱着新娘親熱,大錯便鑄成了。
從此,兩家成了世仇,互相不再來往。
二十年後的一個傍晚,還是那座山,打好兩捆柴的黃柳兒子亮亮和外出賣豆腐的劉旺女兒晶晶遇上了,兩人互不搭理,只顧趕路。這時,天突然瞬間漆黑了,飛沙走石,電閃雷鳴,下起了傾盆大雨。落湯雞似的亮亮和晶晶忙跑進破廟裏,狂風暴雨的夜裏是不能趕路回去的,不但可能遭到猛獸的攻擊,而且還有墜落懸崖的危險。
亮亮很快生起一堆火來取暖,見到晶晶畏縮在角落直打寒噤,於心不忍,便叫晶晶過來烤火。晶晶猶豫了一陣,羞怯地挪到了火堆旁邊。濕透的衣服讓他們感到刺骨的寒冷,連連打着噴嚏,這樣很容易生出病來。亮亮想了一陣子,取來幾根木棒搭了兩個架子,把濕透的衣服掛在架子上,並形成了一道布簾,遮擋了晶晶的視線。晶晶遲疑了片刻,也脫了部分濕衣服晾在另一個架子上,以便快點烤乾。
兩人在火堆旁瑟縮着身子。突然,一道凌厲的閃電伴着隆隆驚雷擊進廟裏,把破廟裏的大香爐都擊碎了。兩人駭然地驚叫,不約而同衝破屏障,相互倚靠着壯膽,兩個幾乎赤裸的身子跌撞在一起。雷鳴閃電不斷,兩人忘了羞怯,身體由顫抖到熾熱,很快便在暴風雨中的破廟裏融為一體。
沒多久,晶晶肚子便微微隆了起來,見不得人。在父母的拷問下晶晶哭哭啼啼地說出了和亮亮在山上破廟躲雨的那一夜。劉旺一聽,腦袋都像被炸開了,劉旺的妻子更是哭得死去活來。夫婦倆關起大門埋頭盤算了一天,左右不是,只好硬着頭皮找到黃柳家。
黃柳夫婦見到劉旺夫婦感到愕然,四目相對,尷尬而羞澀。劉旺吞吞吐吐地說明來意。黃柳一聽腦袋也像被炸開了,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兒子亮亮。亮亮囁嚅着承認了事實。黃柳的妻子一聽,捶胸頓足地哭喊:「造孽啊!」
黃柳是個通達事理的人,深知這事處理不慎就會害得劉旺家破人亡。二十年的恩怨,也是該解開心結的時候了。黃柳動情地說:「大哥,這一切都是天意,讓孩子們盡快成親吧,往後,我們就親如一家了。」劉旺聽後,熱淚盈眶,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一雙大手緊緊握住黃柳的手。
自此,兩家人便冰釋前嫌,親如一家,並且糅合了兩家製作豆腐的技術和精華,將豆腐的質量推到了更高的層次。
又一個二十年,這座山走出了一個大美人,在省城開了家豆腐作坊,做的豆腐清潤滑嫩,成了遠近聞名的「豆腐西施」。
(作者為廣東肇慶懷集人,文學創作三級。二○二○年上榜中國作家網「每周之星」。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
端 硯 ●文河子
不知道一方泥土凝固成石頭
需要經歷多少滄桑和煎熬
從石頭昇華成端州一朵紫雲
是不是消化了肇慶千年的底層苦難
和德行,才能在災難深重的大地
脫胎換骨成為石頭中的貴族
什麼時候開始,石頭深處竊竊私語
大小石眼布滿血絲徹夜不眠
魚腦凍、火捺、蕉葉白和金銀線
各路仙顏雲集,交頭接耳
從老坑,宋坑,麻子坑和梅花坑
繞過西江洶湧的江底,翻山越嶺
深邃的眼神若隱若現
偶爾以閃電和炸裂的形式
坦露隱藏已久的胎記
發布草擬了千萬年的宣言
述說石頭家族蛻變的真相
紫雲升騰到人間
帶來的是甘霖,沐浴肇慶的歷史
滋潤中國書畫文化的墨田
從端州石工苦澀的汗水
到宋徽宗案頭上的宣紙
包拯的正氣到蘇東坡的文才
都有端州硯石行雲流水的足跡
硯石的千言萬語一旦破譯
就演義成肇慶民間不眠的燈火
和夜以繼日的斧鑿聲
演義成勞工商人文人和官家的人生
硯石上的花草蟲魚和風物百相
與墨條清水之間滔滔不絕的絮語
打磨口傳心授書畫的經典
端硯,在文房中出落成謙謙君子
成為越寫越厚重的肇慶文化
(作者原名朱偉全,詩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