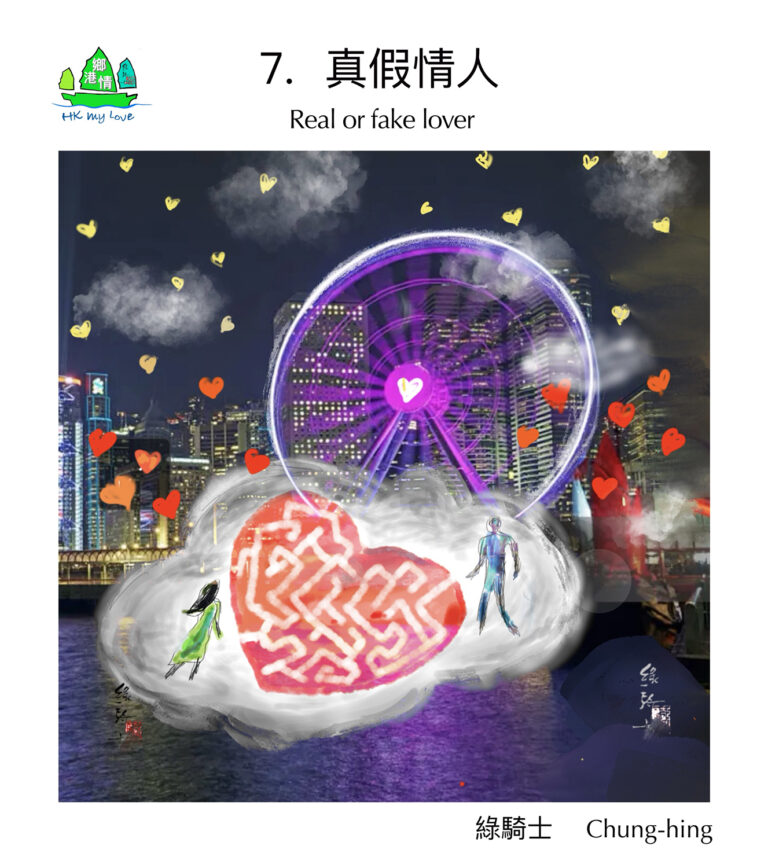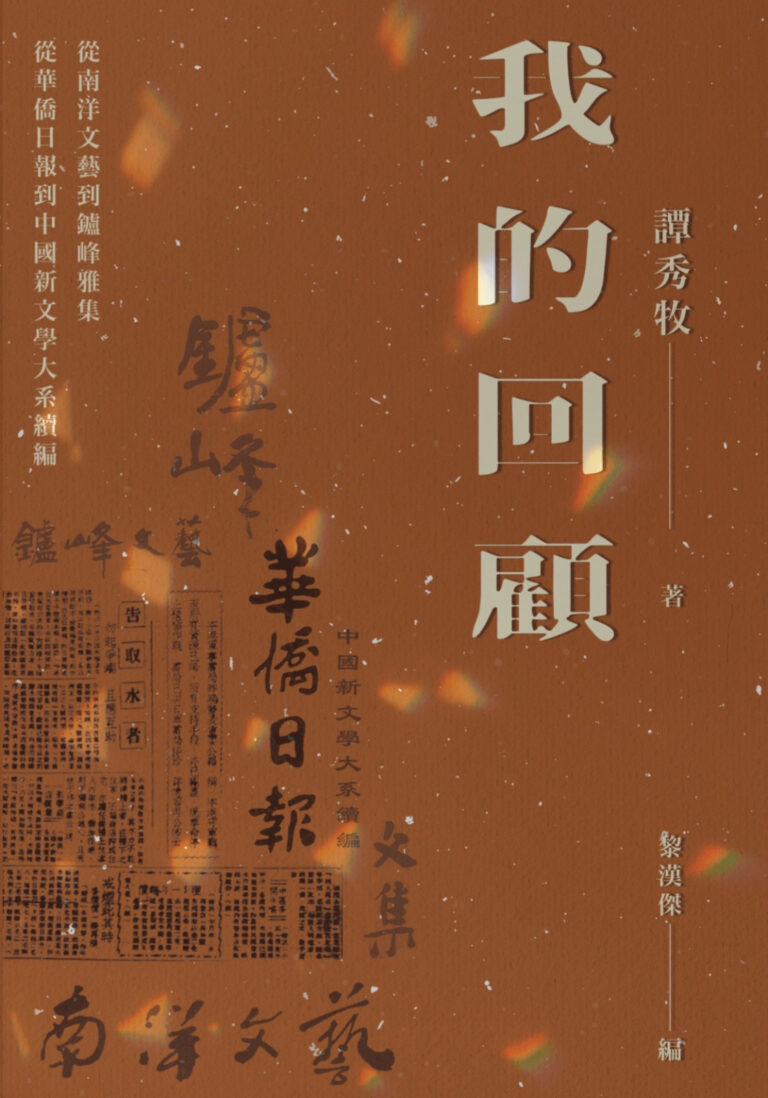編按:廣州文學淵源綿長、內容多元豐富,有着穩定深沉、流動包容、傳統與現代交織、本土與外來共生的獨特氣韻。今期深入剖析。張鴻從小說、散文、詩歌及報告文學四方面勾勒廣州文學的特點與精神風貌;王溱以「爺爺的槍」守護獨居女子的故事,書寫都市驚魂;林培源則從近年以廣州為背景的小說入手,分析多元敘事如何描繪城市風貌與大灣區城市精神。本版主編潘耀明以廣州文學作品分析其地域特色與精神圖譜。
唯有扎根大地 方能仰望星空 ●潘耀明
廣州,這座歷經二千多年文化洗禮的南方都市,始終是漢語文學版圖中一座不可忽視的豐碑。從近代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宣言,到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實踐;從魯迅在中山大學播撒的火種,到當下「新南方寫作」的先鋒實驗,廣州文學始終以開放包容的胸襟、銳意革新的姿態,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的碰撞中,構建起獨具嶺南氣質的文學譜系。
廣州文學的基因裏鐫刻着敢於突破傳統的精神密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歐陽山的《三家巷》以細膩筆觸勾勒出革命洪流中的市井煙火,黃谷柳的《蝦球傳》則通過流浪少年的眼睛,映射出殖民地的複雜肌理。這些作品不僅奠定了廣州城市敘事的雛形,更以「小人物見證大時代」的敘事策略,開闢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路徑。改革開放後,章以武與黃錦鴻的《雅馬哈魚檔》捕捉市場經濟初興時的市井活力,而當下林棹的《潮汐圖》則以魔幻筆法重構十三行的全球貿易圖景——廣州作家始終以文學為鏡,既映照歷史轉折中的個體命運,亦折射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獨特軌跡。
廣州文學的獨特魅力,在於其將市井煙火昇華為美學哲思的能力。葛亮《燕食記》中,一盅兩件的飲茶文化成為百年粵港變遷的隱喻;宥予《撞空》裏海珠橋下的出租屋與生活,精準刻畫出當代青年的精神漂泊。這種「以日常見永恆」的敘事智慧,恰如珠江水的特質:表面波瀾不驚,內裏暗湧深流。更值得關注的是,新一代作家如索耳、路魆等,將粵語方言、嶺南文化等元素轉化為敘事實驗的燃料,使《細叔魷魚輝》這樣的作品既扎根地域,又超越地域,成為探討普遍人性困境的文學樣本。
廣州文學的精神底色,是「雄直」風骨與「市韻」美學的交融。黃禮孩的詩歌在茶樓炊煙與星際漫遊間自由穿行,鄭小瓊以《女工記》為流水線生命賦形,而張欣的都市小說則始終保持着對商業文明既擁抱又審視的辯證姿態。這種「在地性」與「世界性」的辯證,在「新南方寫作」浪潮中尤為凸顯:朱山坡從南方民俗走向非洲荒原,王威廉在科技倫理中注入嶺南思維——他們以文學證明,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
站在嶄新的歷史階段回望,廣州文學始終如珠江入海般:既保有源頭活水的清澈,又敢於在鹹淡水交匯處激蕩出新的生命力。這在在昭示,真正的文學高地不在於標榜地域特色,而在於如何將一方水土的呼吸,轉化為人類共通的情感密碼。這正是廣州文學給予當代漢語寫作最珍貴的啟示——唯有扎根大地,方能仰望星空。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嶺南煙雨入筆端——廣州文學的地域特色與精神圖譜構建 ●張 鴻
自近代以來,廣州始終是中國文學革新的前沿陣地,黃遵憲率先倡導「我手寫我口」,對此後的文學革新運動起到了先驅作用;梁啟超提倡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推動了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新文化運動期間,廣州作為南方的主要陣地,產生了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湧現出一批具有拓荒性質的作家作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新文藝持續發展,不少著名作家都曾在廣州參與革命工作,其中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魯迅在廣州培養了一批革命文藝青年,積極傳播革命思想,成為廣州左翼文藝的鮮明旗幟,成果豐碩。抗戰勝利、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經典佳作頻出,黃谷柳的《蝦球傳》、歐陽山的《三家巷》、秦牧的《花城》、吳有恆的《山鄉風雲錄》、陳殘雲的《香飄四季》、黃慶雲的《刑場上的婚禮》、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等,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南粵作家們積極承擔起描繪社會歷史變革的使命,歐陽山、陳殘雲等老作家筆耕不輟,新一代作家作品如潮湧現,呂雷的《海風輕輕吹》、章以武與黃錦鴻的《雅馬哈魚檔》、葉曙明的《環食.空城》、陳國凱的《我該怎麼辦》、以汪國真代表的「新生代詩歌」等,南中國的文學在中國大地上閃耀着別樣的光芒。
當下的廣州,文學生態生機盎然,各種文學體裁發生了豐富的變化,作家隊伍形成梯級結構,文學作品的個性與時代性交融。
小說創作:多元敘事中的時代鏡像
一、紅色經典與歷史重構
廣州的文學創作賡續傳統,紅色題材與歷史題材仍然是作家們主要的創作方向,但他們更關注歷史背景下的個人和家庭,「以小見大」,以個人命運、家族變遷燭照民族歷史。
劉斯奮的《白門柳》是明末清初錢謙益、柳如是、冒襄等人與時代、命運奮力抗爭的故事,它突破了傳統歷史小說的敘事框架,深入文人心靈世界,被譽為「文化詩魂的史詩」,獲得全國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散文家熊育群轉向長篇小說創作,一頭扎進了「歷史」,寫就《己卯年雨雪》,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嶺南鄉村,兩個中日家庭的遭際。近期出版的《金墟》關注的是百年僑鄉的興衰變遷。他的小說創作有着深刻的歷史洞察、細膩的人文關懷和獨特的敘事風格。魏微曾以短篇小說《大老鄭的女人》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歷經十年完成了長篇小說《煙霞裏》,以主人公田莊四十一年的人生為經緯,用編年體結構串聯起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是一部日常敘事與宏大歷史交織的佳作,有評論家說這是「一部流動的中國社會史」。葛亮是當代華語文學界兼具學術深度與創作鋒芒的作家,以歷史敘事、城市書寫與文化考據著稱。《燕食記》以粵港飲食文化為載體,通過四代廚師的技藝傳承,書寫近百年中國的文明流變。龐貝的長篇小說《烏江引》,以文學之筆破譯歷史的密碼,讓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走出檔案,讓長征精神不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具象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的作者鮑十,定居廣州二十餘年,創作不停滯、不重複,最新出版的小說集《我是扮演者》以日記的形式講述了演員「孟千夫」的從業經歷。他說:「我想把中國歷史『兜』一下,通過對歷史的掃描,進行思考。」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晝夜》以「七十」後王端午的人生軌跡為主線,詳盡描繪了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二○二三年近半個世紀裏個體命運的成長歷程,見微知著,透視社會的演變,折射時代的更迭。
二、城市文學
蒲荔子是廣州城市文學的代表。二十年前蒲荔子以李傻傻為筆名出版了長篇小說《紅X》,首印二十萬冊,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幽靈作家」。這本書被稱為「八十後版的《麥田裏的守望者》」,是一代年輕人的青春記憶。二○二四年,他帶着新作《虛榮廣場》回到文學現場,仍然是以「粗烈的蠻力」,描述那些終究不會通情達理的親情、愛情和友情,探討成長的虛榮與真相。居住在廣州書寫廣州的河南人宥予,二○二三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撞空》,以對都市青年虛浮感的精準刻畫而獲得刀鋒圖書獎頒發的年度青年小說家獎。他的語言獨特、敘事具有實驗性,作品主要以都市青年精神困境為創作主題,他的作品與張欣的小說一樣有着具象的嶺南地域細節。
張欣幾十年如一日講述着她生活的這塊土地的故事,《浮華背後》、《深喉》等作品聚焦廣州職場生態,《鎖春記》、《不在梅邊在柳邊》書寫都市女性的命運,近期出版的長篇小說《如風似璧》更是將筆觸延伸到了民國時期,打造了三位女性的不同成長道路。同樣為廣州代言的還有張梅的《破碎的激情》、《遊戲太太團》,這些作品成為中國都市文學的重要文本。
三、「新南方寫作」
「新南方寫作」自誕生以來,它就被投以超越邊界、多元融合的空間性與創新性的理論期待。
在地的代表作家有朱山坡、王威廉、陳崇正、路魆、索耳、梁寶星等。朱山坡的最新小說集《薩赫勒荒原》的出版,拓寬了寫作路徑,讓他的文學地理版圖一直延伸到了非洲、美國,他探索的是人類命運中的靈性交集。王威廉是「八十後」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以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科技倫理、嶺南地域文化為焦點,兼具哲學思辨與敘事實驗,為「新南方」的寫作注入了獨特的智性色彩。近期出版的《火苗照亮宇宙:暗生命傳奇》力圖在宇宙的極限中找到一條新的生命之路。陳崇正的作品譜系龐大,融合了鄉土記憶、科幻寓言、嶺南文化。評論家謝有順曾說:他讓潮汕的「鬼氣」有了當代文學的形貌。
路魆、索耳、梁寶星都是「九十後」作家,路魆的作品充斥着潮濕的黑暗、破碎的夢境與心理深淵,最近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吉普賽郊遊》。索耳雖然年輕,但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的文字猶如一場語言的煉金術,以實驗性寫作重構地域文化敘事,為嶺南文學注入了海洋性的流動感。梁寶星的文學創作以多元主題、創新敘事和獨特語言風格形成鮮明特色,代表作有《海邊的西西弗》等,兼具現實關懷與先鋒探索。
散文創作:從鄉土到都市的精神還鄉
一、歷史鈎沉與文化觀察
筱敏的散文是一代人精神突圍的文學見證。她拒絕隨波逐流,選擇在歷史的暗角與個體的深淵中獨自勘探,以文字為燈,照亮被遺忘的人性微光。她的《捕蝶者》、《喑啞群山》以詩性語言重構了歷史記憶。艾雲被視為「新散文運動」的重要實踐者,她的散文常以個人生命經驗為基點,融入對歷史、文化、自然與人性的深度觀照,展現出一種詩性與理性交織的美學特質。
二、都市觀察與日常美學
葉曙明是兼具文學性與學術深度的複合型作家,其創作以嶺南歷史文化書寫為核心,融合小說、散文、歷史非虛構等多種體裁,《廣州傳》詳盡描繪了廣州城市物質與精神的演變歷程,將地方誌的嚴謹與小說的靈動結合,創造了「學術散文」的新形態,重構了城市書寫的美學秩序。黃愛東西是資深媒體人,「小女人」散文流派的重要作家,作品粵味醇厚,敘事寫人極有作派、腔調,有畫面感。她的散文創作在市井煙火與都市脈搏的交織中,構建起獨特的文學坐標系。
詩歌創作:雄直傳統與現代性突圍
在廣州文學界,黃禮孩是一個標誌性人物,他以自辦詩歌刊物《詩歌與人》為支點,以「一個人的詩歌獎」攪動了整個國際詩歌圈,並以一己之力主導「廣州新年詩會」,持續了十七年。他的作品既延續了嶺南文學的煙火氣,又以跨文化的視野拓展了南方寫作的精神維度,形成了「在地性與世界性辯證統一」的美學特質,代表作品有《我對命運所知甚少》、《我的地理的光明旅行》等。世賓在二十年前提出「完整性寫作」的理論概念,他認為,詩人需以「良知、尊嚴、愛」為基底,建構完整的詩歌人格,十年後他又提出「境界美學」,強調詩歌應觸及「生命意識的最高境界」。代表作有《交叉路口》、《目標在尋找它的神槍手》等。鄭小瓊的詩歌是工業文明的疼痛備忘錄,也是底層生命的精神突圍史。她將個體經驗昇華為時代寓言的寫作,使她成為當代中國打工文學的標杆詩人。代表作品有《女工記》、《庭院的鳥群》等。馮娜是少數民族詩人,曾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她的創作將滇西北的自然神性、多民族文化記憶與現代性反思熔鑄一爐,形成了兼具詩性凝視與哲學思辨的獨特風格。代表作品有《無數燈火選中的夜》、《樹在什麼時候需要眼睛》等。
報告文學與「非虛構」
劉迪生是當代廣東報告文學領域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以「大寫生命、記錄時代」為核心,聚焦改革開放前沿的社會變遷與人物命運。他的代表作品《南國高原:徐克成和他的醫學世界》、《點亮生命:志願者趙廣軍感動中國》等,可以看出他對生命的敬畏與對時代的擔當,使其作品超越了文體的局限,成為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文本。黃燈是「非虛構」的重點作家,她的作品〈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曾經在各大公眾號閱讀量超千萬,成為「返鄉書寫」的代表性文本。她以個人體驗創作的《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聚焦鄉村現實、教育公平,相繼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廣州文學以「雄直」、「風骨」、「市韻」為基底,多維度持續突破,既扎根嶺南本土,又面向全球視野,形成「傳統與現代交織、本土與外來共生」的獨特氣質。未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廣州文學將在更多的領域開闢新境界,成為中國文學版圖中不可替代的「南方坐標」。
(作者為《廣州文藝》、《詩詞》報總編輯,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