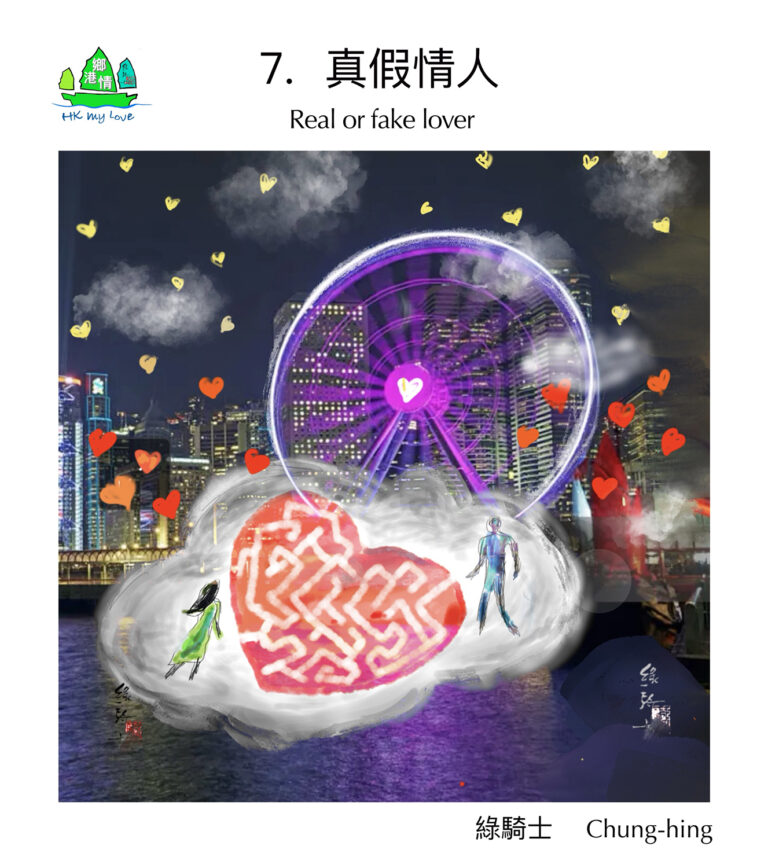編按:近年大灣區發展備受矚目,新界西正是其重要一環,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各具特色風貌。嶺南大學中文系各體文類習作課程學生以此為題作了一系列創作,描繪新界西的城市變遷與風土人情。本版特精選數篇學生作品刊載,並配以課程導師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師陳偉中博士評語。習作或見青澀,然觀察細膩,感情真摯,足見他們對這片土地的情懷。
石階垂絮時 ●黃子璇 中文系二年級
青銅色的黎明
刺入羊城的褶皺
你繾綣在珠江鹹澀的潮音裏
在光緒年的凍土下
倔強,翻身
而我
由珠江的紋路撫育
聽江水輕吟你往昔的足跡
從石牌坊書頁沙沙
到仙人廟晨鐘嫋嫋
輕輕
在我耳邊迴蕩
在香港的季風裏轉身
你已是石階上的古榕
我也蛻成木棉的飄絮
緣份將羊城的銅綠
焊入你褪色的指紋
論文……
彙報!!!
Deadline——
遊標在午夜抽搐
鍵盤捶打黑鐵的寂靜
圖書館的太陽
撫平瞳孔裏的廢墟
在你鐫刻滄桑的年輪裏
我開始鍛造自己的史詩:
銀河垂落於筆尖
如同夜空的細語
將未敘的嶺南
淬進硯底……
導師陳偉中評語:此詩以嶺南大學與廣州的歷史淵源為背景,透過時空交錯的意象(如珠江、石牌坊、仙人廟)建構個人與學校的記憶連結。意象以「青銅色黎明」「光緒年凍土」等意象,將個體成長嵌入嶺南歷史脈絡;結尾突轉至「Deadline」「鍵盤捶打」,在傳統與現代張力中探討學術壓力與精神傳承的關係。創新嘗試:將地理歷史意象(銅綠、榕樹)與數位時代符號(遊標、鍵盤)並置,形成陌生化對比。
迷失鐵路 ●李健誠 中文系二年級
點滴沿耳機線注射進大腦
玻璃月台記錄着沉溺者的輪廓
指頭反覆摩擦
直到晨昏線縫起眼瞼叮噹——
離開車廂
春風隔開天橋上的衝突
吹拂麻雀的鳴歌
縈繞孩子們的天真與幼稚
韶光輕吻少年的羽翼
繞行雨後軒的殷紅年輪
想追捕鐵灰貓尾
晃過一圈,兩圈,三圈……
四年刮痕
鉻在玻璃表面上
軌道在角膜內飄散成
彩虹色迷霧
閘門開,又合
我乘着末班車駛向
地底深處的
未知盡頭
導師評語:此詩以地鐵車廂與校園的自然/人文景觀為對比,探討現代人被科技異化的麻木狀態(車廂)與鮮活生命力(校園)的衝突,最終回歸對未來的迷茫。嘗試通過:空間轉換(車廂、天橋、校園)建構敘事層次意象對立;(科技/自然、僵/生機)強化主題張力時間隱喻;(貓尾、年輪、四年刮痕)表達青春易逝。唯「四年刮痕/鉻在玻璃表面」中「鉻」(金屬)與時間痕跡的關聯不夠自然。
圍——新界西生活記 ●鄺玉齡 中文系三年級
初來香港時,我住在天水圍。
那時只覺得這城市像一隻巨大的鐵籠子,將人密密實實地關在裏面。屋苑樓與樓之間挨得極近,從我家窗口伸出手去,幾乎能碰到對面人家的晾衣桿。
母親總說我們幸運,住的是私人屋苑,比公屋寬敞些。但所謂「寬敞」,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罷了。
四口人擠在三十多平米的空間裏,轉身都要預先打招呼。弟弟的玩具和我的書本常年爭奪着沙發底下那點可憐的儲物空間,勝負難分。
天水圍的街道像是被人用力捏過的紙條,皺巴巴地蜷曲着。行人道上永遠擠滿了人,大家摩肩接踵地走着,卻都默契地保持着一種奇異的沉默。
初來時我很不習慣,總覺得這麼多人卻如此安靜,實在詭異。後來才明白,在這方寸之地,沉默是最體面的相處之道。
上屋苑會所的設施清單看起來很長:游泳池、健身房、閱讀室……
實際每個都小得可憐。游泳池像個大浴缸,擠滿了學游泳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健身房裏三台跑步機永遠有人在用;所謂的閱讀室不過是個擺放了十幾本書的玻璃櫃子。
周末時,我和弟弟常常在屋苑裏轉上好幾圈,最後只能坐在大堂的長椅上發呆。
母親說我們在內地時抱怨城市太大,去哪都要坐車,現在又嫌地方太小無處可去,真是難伺候。
就這樣過了七年。七年裏,我和弟弟都長高了,家裏的東西也像會繁殖似的越來越多。終於有一天,父親看着弟弟的自行車,卡在門口進不來的樣子,嘆了口氣說:「搬吧。」
我們搬到了元朗的村屋。雖然離天水圍不過幾站輕鐵的距離,卻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
村屋沒有會所,沒有管理員,開門就是街道。第一次站在三層小樓裏時,我竟有些不適應——原來伸直手臂真的可以碰不到牆的。
其實在天水圍住時,我們就常來元朗。每個周六,我都要去喜利大廈上鋼琴課。
最初,覺得元朗像個迷宮,那些橫七豎八的小巷彷彿會自己變換位置。大馬路旁突然岔出的小路,走着走着又分出幾條更小的岔道。
我常常在找路時誤入一些奇怪的地方:藏着老式茶餐廳的後巷,堆滿五金雜貨的騎樓底,甚至是某戶人家的後院。
有次為了找近路,我鑽進一條小巷,結果繞了半小時才回到大路上,鋼琴課早已開始。奇怪的是,這種迷路的經歷並不讓人煩躁。
在天水圍,迷路是不可能的——每條路都筆直地通向某個明確的目的地。而在元朗,迷路反而成了探索的樂趣。
大約兩三年後,我突然發現自己不再需要導航了。那些曾經看似相同的街道,在我腦中已經自動繪製成了一張立體地圖。
但真正了解元朗,還是搬來之後的事。村屋的生活讓我有了更多閒逛的理由和機會。不用再像從前那樣,每次來元朗都匆匆趕去某個特定地點,然後又匆匆返回天水圍的「圍城」裏。
我開始注意到元朗的肌理:以青山公路為中軸,向兩側延伸出無數毛細血管般的小街巷。輕鐵像一條銀色的絲帶,將這些脈絡串聯起來。
元朗的豐富是慢慢顯現的。朋友第一次來我家玩時,驚訝地說:「你們元朗怎麼什麼都有?」我這才意識到,原來在不知不覺中,這裏已經能滿足生活的所有需求。
想吃地道的?街市旁的老字號粥粉麵店開了三十年;想喝奶茶?方圓百米內能數出五家不同品牌的店;就連寵物都有專門的街區,從糧食到美容一應俱全。
最妙的是,這些店舖並非整齊劃一地排列在商場裏,而是隨意地散落在街巷各處。轉角可能遇見的不是愛,而是一家開了四十年的涼茶舖。老闆不用問就知道你要喝什麼——元朗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涼茶偏好,我家樓下那家記得我父親總要「廿四味加甜」,母親愛「雪梨茶走冰」。
輕鐵是元朗的脈搏。住在天水圍時,我覺得輕鐵只是交通工具;現在才明白它是元朗人的生活時鐘。
清晨趕着上班的人潮,下午主婦們買菜時的悠閒步伐,晚上補習學生匆忙的腳步,都在輕鐵站裏交匯。我常想,若是把元朗的輕鐵路線圖疊放在舊時的水系圖上,大概能重合個七八分——人們依然沿着水的軌跡生活,只是鐵軌代替了河流。
五年過去,我已經能像本地人一樣,在街市裏挑最新鮮的菜,知道哪家茶餐廳的菠蘿油最好吃,甚至能說出幾條只有老元朗才知道的捷徑。
帶朋友逛元朗時,我像個炫耀自家後院的孩童,一定要帶他們去吃我認為最好吃的雞蛋仔,走我認為最有味道的老街。
朋友常說元朗人幸福,我想他們說得不錯。這種幸福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一切都恰到好處地存在着——不至於多到讓人眼花繚亂,也不會少到令人捉襟見肘。
就像我家村屋的天台,不大不小,剛好夠擺四把椅子和一張小桌。傍晚時分,我們一家常坐在那裏,看着輕鐵從遠處駛過,車燈在暮色中划出一道流動的光痕。
從天水圍到元朗,不過是從一個「圍」到了另一個「圍」。但這兩個「圍」字,卻有着天壤之別。一個是困住人的圍城,一個是圍起來的家園。
導師評語:此文透過對比天水圍與元朗的居住體驗,探討「圍」的兩種意義「圍城」與「家園」。作者以細緻的觀察展現香港新界西的市井生活,既有對空間壓迫的批判(天水圍),也有對社區溫情的讚美(元朗),最終落腳於「家」的歸屬感。主題兼具社會性與個人性。中間過渡稍顯突兀(如「就這樣過了七年」後可加入承接);元朗部分的「迷路」段落可更緊密銜接後文的「探索樂」。

牛牛幻想曲 ●莫嘉瑤 中文系三年級
我聽見。哞——
天然的鬧鐘響起。我套上制服時,鄰居張師奶牽着她的霍爾斯坦牛路過窗下,牛鈴叮噹混着她尖銳又急速的嗓門:「落街飲早茶要趁早等陣天水圍班塞牛大軍殺到屯門公路又要打蛇餅!」
噠。噠。噠。
眼前的景色是這樣的:戴金絲眼鏡的銀行經理騎着娟珊牛,西裝口袋插着《星島日報》,牛角掛着Starbucks外帶杯,全身上下無一不精緻。穿緊身運動褲的師奶駕馭印度瘤牛,牛背上綁着剛出爐的菠蘿包,麵粉香與牛糞味在輕鐵站前交纏。最威風的還得是地產經紀,他們跨坐通體雪白的氂牛,牛蹄包滿金邊,蹄鐵敲擊青磚路面的節奏,令人血脈賁張。
以上……
只是我的想像罷了。
我曾堅信遙遠的西新界人血液裏流淌着牧草汁液。中三那年在地理課本空白處塗鴉,將輕鐵路線圖改畫成牛種分布圖。我想,610線是霍爾斯坦牛,溫吞但準時;507線是印度瘤牛,脾氣暴躁卻腳程快;506P線嘛則是雜牌老黃牛,年老又不能缺少的存在。
直到那一年——
我來到了,屯門。
那天我站在屯門市廣場天橋上數了整整三小時,穿梭而過的只有九千六百七十二輛汽車與四十三架單車。還有,零隻牛。
原來,關於牛的記憶,終究是都市傳說嫁接的枝椏。
然後,我坐上了輕鐵,507。輕鐵慢慢行駛,駛過V city。我又想起了那個曾經反覆出現的畫面。一個男孩騎着牛從屯門輕鐵站穿越V city,最後在一田櫥窗前表演急停,還記得避開拖着粉紅行李箱的水貨客。
精彩。
為此,我還特意製作了一份《屯門牛路守則》。《屯門牛路守則》第三十七條:
「牛隻進入V city須佩戴防撞角套,以免刮花名店櫥窗倒影」。
以上……
不過是我的想像罷了。
車廂裏飄浮着不同語言的交談聲,韓妝少女與跨境學童共享着搖晃的扶手桿。
我將額頭貼上玻璃窗,看那些曾幻想牛隻奔馳的街道——
經過蔡意橋。不知誰家陽台飄來蒸鹹魚的香氣,混着巴士的柴油味,在屯門河面織成半鹹淡的霧。輕鐵的影子隨着腦海中的幻想越拉越長,越來越長,漸漸蓋過整個屯門,最後消融在晨霧之中。
某天下班我去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辦理護照,在輕鐵站邂逅牽牛隻散步的老伯,牛隻頸上繫着銅鈴。「唉,幾時先可以儲夠錢,將呢隻老牛換架車。」話畢,只見身旁的一隻牛突然撅起後蹄,將阿伯的漁夫帽踢進屯門河。
以上……
可能又是我的想像?
那只是一隻調皮的大狗踢翻主人的帽子——那頂浮沉的帽子像一片牛糞,順着水流漂向對岸正在施工的新樓宇?
《屯門牛路守則》第五條:「牛隻造成異物入河事故,須繳交牛蹄清潔費,並暫停該牛隻上路資格一年。」《屯門牛路守則》第六條:「牛隻不得不……」又扯遠了。
以上……
又再是我的想像罷了?
晚飯過後,我總是喜歡在屯門遊蕩。從兆康走到新墟,從藍地走到麒麟,從屯門碼頭走到蝴蝶灣。而往往這時候,總會看見騎行單車者們蜿蜒如緞帶,閃着車頭燈組成一道流動的彩虹。
我忽然羨慕起那些踩單車的人。
在九龍區長大的我很少接觸單車,甚至想在市區中心尋覓單車的蹤影,也不見一輛。說來慚愧,我竟不會踩單車。他們在輕鐵站旁的金屬架前彎腰解鎖,動作嫻熟如西部牛仔繫韁繩。
這,或許才是屯門真正的「牛」。
當市區人為找不到泊車位苦惱時,這裏的屋邨總能從角落變出纏着膠帶的單車架,生鏽的鋼管上開出歲月的鐵鏽花。
每天坐上62X巴士來往屯門與九龍,看着陽光在車廂地板上切割出明暗方格。
此刻,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身穿正裝的女士正用手機拍攝沿途街景,河畔開滿紫荊的單車徑,天橋下玩滑板的少年,商場外牆輪播的電子廣告。當車輛轉入隧道時,玻璃窗突然變成鏡面,映出我們這群沙丁魚乘客的疲憊面孔——那些幻想騎牛上學上班的執念,或許只是對邊陲地帶的一種迂迴想像。
我終究沒見過傳說中的「塞牛大軍」。
下車後,看見穿瑜伽褲的母親拎着Donki環保袋走來,她身後正是舉辦美食節的屯門市廣場。我們穿過停滿單車的屯門公園,不鏽鋼車架在夕照下燃成一片金屬草原。暮色中有人騎着單車掠過,車輪輾碎我投在地上的影子。突然我清楚看見生銹踏板旋轉成青銅牛鈴。那一瞬彷彿瞥見騎牛少年在公路上慢悠悠地晃悠,我眼巴巴地仔細盯着那牛背上晃來晃去的身影,而牛蹄揚起塵土,夕陽正將背後的輕鐵軌道鍍成金黃的韁繩。此時河面漂來的塑膠帽忽然立起尖角,而母親購物袋滲出的血水正灌溉着水泥縫隙。我終於聽懂——那徹夜不休的「哞」聲,原是整個城市在反芻自己的鐵胃。
導師評語:此文透過「牛」的虛實交錯,隱喻都市化對地方文化的消解,主題新穎且富詩意。但「單車替代牛」的轉折稍顯突兀,可加強連結(如單車鈴聲與牛鈴的呼應),中段《屯門牛路守則》重複略顯冗贅,可精簡條目或融入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