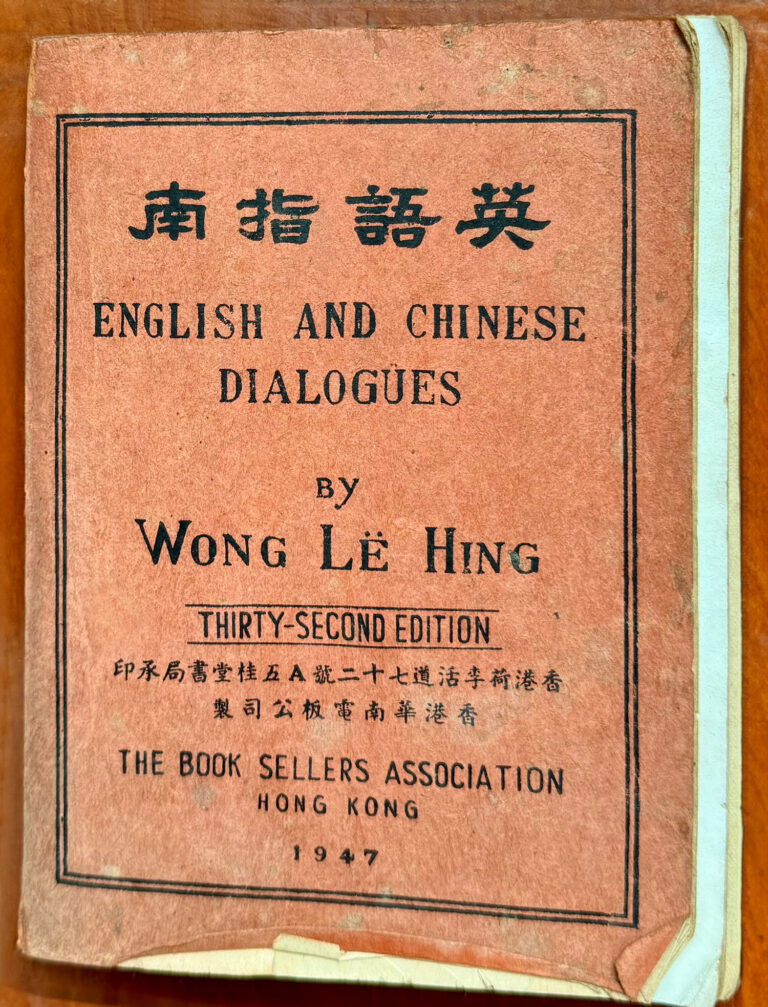编按:今年不仅是金庸先生诞辰百年,也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先生诞辰百年,适逢此机缘,本刊特组织专题,以兹纪念。本版主编潘耀明综谈梁羽生与金庸这两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侠亦文」的好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和文缘纠缠,并寄望香港对梁羽生百年诞辰应予以重视。梁羽生为了创作出好的小说作品,将自己的文学素养、对历史的研究和各种杂学加以运用到写作中,为武侠小说带来一番新气象。文学博士陈瞻淇致敬这位「侠情遗韵在人间」的「博观约取真才子」。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陈墨析论梁羽生对新派武侠开山之功与重大影响、作品中文人小说和成年人的童话之特性,以及一次与梁羽生相见、同行、对谈的难忘经历。
没有梁羽生的日子●潘耀明
今年有两个武侠大师诞辰一百周年,一个是金庸,诞生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另一个是梁羽生,诞生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梁羽生的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写于一九五四年,一炮而红;金庸《书剑恩仇录》于一九五五年开笔,一举成名。梁羽生一九五四年开始共写了卅五部武侠小说,金庸一九五五年开始共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
从以上简单资料的胪列可知,梁羽生是先于金庸一年写武侠小说的。以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而论,非梁羽生莫属。
公道地说,没有梁羽生也没有金庸。金庸是后来者,而且是后来居上的。金庸在梁羽生逝世时拟了一段梁羽生的话说:「明明金庸是我后辈,但他名气大过我,所有的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作品好过我。」虽是金庸写的话,却说到梁羽生的心里去了。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梁羽生对此一直是忿忿不平的。他曾化名写了〈金庸梁羽生合论〉,用以扬梁抑金,大大吐了一口乌气。只是这篇文章后来被人戳穿了,对梁羽生来说,就有点不好玩了,不免为人所诟病。平心而论,梁羽生的旧学根柢是比金庸要好,诗词歌赋楹联样样精,这是金庸自己所承认的。
金庸曾写道:「后来他(梁羽生)应《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兄之约而写《龙虎斗京华》,我再以《书剑恩仇录》接他《龙虎》之班,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后,陈凡接写一部武侠小说,我们三人更续写《三剑楼随笔》,在《大公报》发表,陈凡兄以百剑堂主作笔名。武侠小说不宜太过拘谨,陈凡兄诗词书法都好,但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了。所以他的武侠小说没有我们两个成功。」金庸说陈凡武侠小说写得不好的毛病,或有他对梁羽生武侠小说借山打石的隐喻,梁羽生武侠小说也有用典过多的毛病。
金庸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孰优孰劣,其实读者最是心水清。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梁羽生是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先河的一代宗师。他的武侠小说没有金庸写得好,但他的作品也曾拥有广大的读者。有一次文友相聚,谈起林青霞与张国荣主演的《白发魔女传》可谓双剑合璧,端的是神乎其技,特别是水畔挑情的一幕,看得人如痴如醉。我当场表示作者梁羽生也应记一功。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也是梁羽生诞辰一百周年——金庸先他半个月而生,在梁羽生写作及工作大半生的香港,却乏人提起他,无声无息。从政府到民间,对金庸百年诞辰的庆贺活动闹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对梁羽生竟然只字不提,令人大惑不解。倒是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了一场「百年梁羽生.永存侠影在人间——纪念梁羽生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稍可告慰这位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地下之魂!
有南京雕塑家陈建华,通过钢琴大师刘诗昆转达说要捐赠一座金庸雕塑给香港文学馆,我让刘大师代转话情商陈先生再造一座梁羽生的雕像。这位艺术家果然爽快,一口答应,在很短时间内雕了一座梁羽生雕像,让这两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侠亦文」的好友在香港文学馆并肩而立,共话桑麻!
(作者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明报月刊》荣誉总编辑、本版主编。)

高72厘米青铜2024
(陈建华雕塑工作室提供)
孤怀统览任平生——写于文统公百年诞辰之际●陈瞻淇
北宋易学家邵雍曾有诗句云:「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挥麈时。」套用至陈文统先生之创作,可称为「生公非是爱武侠,侠是生公挥麈时」 。
博观约取真才子
陈文统先生学识渊博,谙熟历史、诗词、对联、掌故、围棋、象棋等,是著名作家、楹联学家和棋评家,于文辞一道涉猎极广。数十年来在报纸上开设多个专栏,除武侠小说上千万字外,其各类专栏文章亦上千万字之巨。
先生于一九八四年封剑,封的只是三十年来的「笔荡江湖」生涯而非就此封笔,仍然继续数十年来的文史小品写作,陆续刊载于香港《大公报》、《香港商报》、新加坡《星洲日报》等,笔耕不辍。他并未另起炉灶而独掌一门,而是远离政治和商业,如中唐元白「元和体」般,「其间感物寓意,可备蒙瞽之讽达者有之,词直气粗,罪戾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由此陆续如写武侠小说般刊发,再结集出版,有《笔.剑.书》(一九八五)、《笔不花》(一九八六)、《名联谈趣》(一九九三)、《笔花六照》(一九九九)、《笔花六照》(增订版,二○○八)等。
先生用功最勤、贡献最大的是楹联的创作与研究。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设了三年四个月的每天见报的「联趣」专栏,后结集为《古今名联谈趣》(一九八四),《名联观止》(增订版,二○○八)分上、下集,《名联观止》(二○一七)增补《香港商报》的「联上趣」专栏内容而使其「联话」更为完整。先生武侠小说回目精工巧妙,可作为名联集锦品鉴。
先生长于诗词创作,仅小说中的开篇词、终篇诗及书中间涉诗词便足结成厚重专集。故此乃有二○○八年杨健思辑录之《统览孤怀——梁羽生诗词、对联选辑》一书,分为「少年词草」、「弹铗歌」、「剑外集」三部分,选录先生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初期的诗词作品、武侠小说中及此外的部分诗词和对联。先生知交邝健行教授在该书序中特地提到:「总览先生着册,多纳诗词。所以抒角色之感兴,所以助情节之推移。非撏撦于义山,乃推敲之旡本。风貌去昔贤,未逾尺咫;文辞见他作,颇讶马牛。盖先生少炙名家,早通律调。每能寄意,尤擅倚声。往往摇曳清泠,飞冷香于秀句;啸吟枨触,忆故剑之平生。至味堪寻,一时莫比。然而虽遵章回之轨辙,亦寓时代之精神。……若夫先生联语之雅文律切,回目之工稳意赅;此特诗词之余艺。茂根而遂宝,沃膏而晔光;可以不烦论议者矣。」结合该书收录诗词统观之,先生词宗南宋白石、玉田以来的清空一派,古雅峭拔,清丽婉约,在意象、色调、抒情方式上独具一格,展现出狷洁的文化人格。先生在小说正文中大量运用诗词楹联(包括小说名与回目),不仅文采斐然,对渲染环境、交代背景、促进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等都能起到推动作用,甚至成为情节转捩关键,并且平添了文人雅致,提升了小说意境与格调。尤其是开篇诗词或者结尾诗词,都能奠定全篇基调和总结提炼全篇主题,有意味深长、韵致悠远之美学意蕴。
先生采用多个笔名,撰写各类文史小品。比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开始使用「陈鲁」的笔名,用于围棋、象棋的棋话与棋评,出版有《穗港棋王会战纪详》(一九五五,署名陈鲁,与王兰友合着)等;一九八○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以「时集之」的笔名在香港《商报》开设专栏,其间一九八六年一月初至一九八七年五月底的「摘录评点《金瓶梅》」专栏以每日一篇的量累计三十二万余字,后结集为《梁羽生闲说金瓶梅》(二○○九);四百多篇谈论民国时期诗词作品的文章后结集为《梁羽生妙评民国诗词》(二○一六)。
其他笔名,如以「梁慧如」写历史小品,以「冯瑜宁」写文学随笔,以「李夫人」之名主持「李夫人信箱」等,这些散文、评论、随笔、棋话,后结集为《史话一千年》(一九五四,署名梁慧如)、《婚姻与家庭》(一九五五,署名冯浣如)、《文艺杂谈》(一九五五,署名冯瑜宁)、《人生与友谊》(一九五五,署名冯浣如)、《中国历史新话》(一九五六,署名梁慧如)、《三剑楼随笔》(一九五七,与金庸、百剑堂主合着)、《李夫人的信》(一九五八,署名冯浣如)、《古今漫话》(一九六九,署名梁慧如)、《人生的探秘》(一九七二,署名冯浣如)、《文艺新谈》等。此外还有「冯显华」、「幻萍」、「佟硕之」、「凤雏生」等笔名。
境界始大开新派
先生早年立志从事文艺工作,后来也以文艺小说的标准来创作武侠小说。
他曾指出武侠小说完全可以符合文艺小说的要求,即反映时代、塑造典型人物及艺术感染力。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 「写好武侠小说并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请作「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演讲时,介绍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先生一贯主张,武侠小说的创作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文化储备。仅仅把文本和形式当作突破口,对传统文化、对历史、对文学没有真正认识的作者,是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来的。从这一点反观先生的武侠小说创作,就会发现既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形式和审美,又摒弃了传统武侠小说一味复仇、嗜杀的倾向,将现代的历史政治观念融入武侠小说;不仅将传统小说中诗词、回目等艺术形式大加发挥,而且提出「以侠胜武」的创作观念,赋予「武侠」新的含义,将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类型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先生撰述武侠小说时受到当时文学政治观念的影响,创作中展现出以人民性为本位的侠义观,几乎每部都在明确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从唐至晚清,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宏大江湖世界和历史谱系。主人公多能做到侠义精神与历史责任的统一。所以他笔下江湖义士较少,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历史英雄较多,一新明清以来白话小说英雄人物为官府、帝皇权臣分忧之风气,极具现代意义。由此,他笔下不仅有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名士游侠,亦如《红楼梦》般刻画出一批智勇美兼具并勇担重任、远胜须眉的女性形象。
但开风气不为师
与此同时,宏大叙事下乃有师老兵疲之弊,比如模式化的创作倾向,主题和人物性格的单一,对人性世态的描摹偏于浪漫而缺深刻,传统白话小说创作那种枝节曼衍、说教甚重的笔法在其后期创作中也多有体现,等等。
中国武侠文学研究专家陈墨在二○○九年缅怀先生的〈情怀梁羽生——莫道萍踪随逝水〉中写道:
阅历深厚而才华横溢,偏率性懒散而不善经营,的确是生公大侠为文和为人的重要特征。若善经营,其小说艺术张力可发挥到另一重天地;若不懒散,而对其小说进行必要的修订整理,则其小说必更少瑕疵而更多精彩,侠迷梁粉必有更多可探讨可赞叹的话题。小说之内如此,小说之外亦如此,梁园虽好,其值不彰,未尝不是缺少内外经营之故。
这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心态,学养丰厚、才气非凡却始终心有旁骛,终致先生仅成就一代武侠小说宗师之名。
先生心思纯挚,秉性率真温厚。中山大学冼玉清教授说他「忠厚坦挚,近世罕见」,可视为不通世务的另一说辞。香港诗人舒巷城赠诗「裂笛吹云歌散雾,萍踪侠影少年行。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诗中的末句,令先生大呼「知我者,巷城也」。识者则以为如此书生品质,做学问或写诗或许是美质良才,作为小说家则未免有所欠缺,这也许就是先生武侠小说中创作主题、人物刻画、情节场面等过于单一的根源所在吧。再就是陈墨先生在《香港武侠小说史》中所指出的:「在独立意志、独立个性追求,以及独立思考勇气、习惯和能力等方面,梁羽生与金庸有很大不同」,加之创作中后期如同还珠楼主般鱼龙曼衍,互文迭出,终致艺术表现效果打了折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期找不到修订出版《武林三绝》的恰当方案。
侠情遗韵在人间
先生曾有集句联:「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此联既暗嵌「文统」、「羽生」之名,又是他的人生写照。 「侠骨文心」为其武侠主题亦寓其为人要义,「孤怀统览」见其庙堂之高廊庑之大,将其平生情怀抱负、功业感慨悉纳此联。他开创了一个新武侠繁荣的时代,是一位真正彰显中国武侠文化的大师。
二十年前,也就是二○○四年六月,先生在《笔花六照》再版后记中回顾创作生涯,写道:「往事并不如烟,要说是说不完的,能说多少就多少吧。这正是:旧梦依稀记不真,烟云吹散尚留痕。」话语一如既往的低调,却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以及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为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文学博士、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