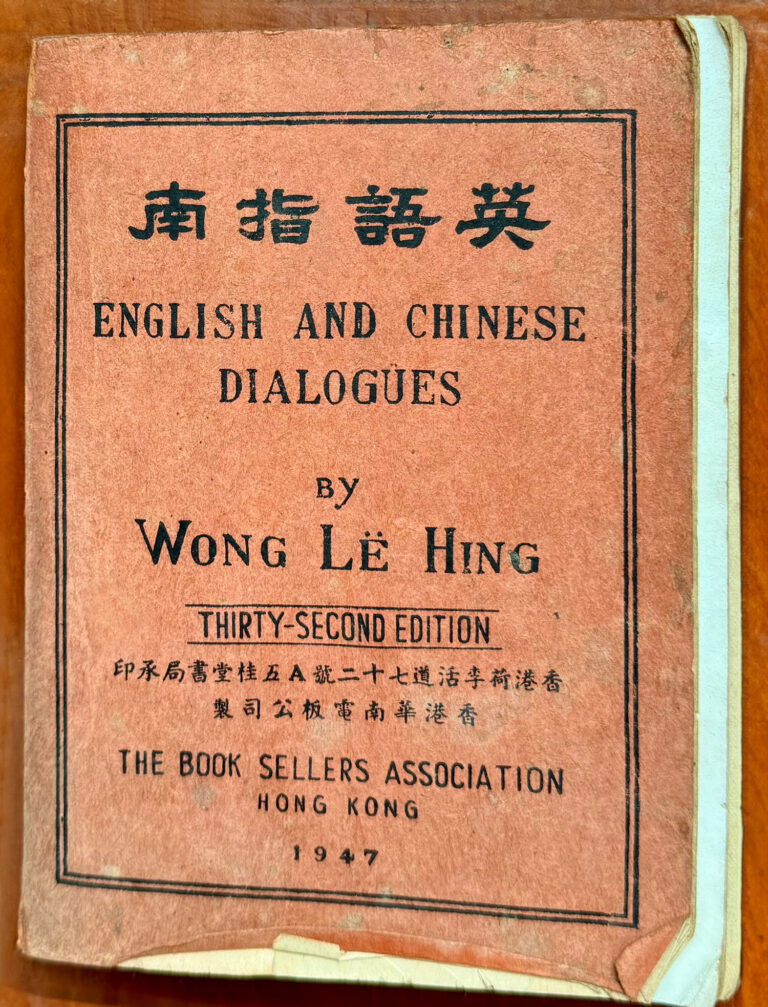不是你一个人活得丧丧的●张欣
前几天有一个轻松的聚会,吃东西闲聊那种,而且是居家没有着装要求,一开始大家都兴高采烈,吃完饭集结在茶桌上展开深度聊天,发现每个人都很丧。有正在离婚的,有家中老人痴呆的,有自己身体亮起红灯的,有重度失眠的,有跟顶头上司极度对抗又不能辞职的,还有争夺遗产打官司的,以及一个朋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实现了梦想轻飘飘来一句那不是我想要的。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大叹苦经,因为我是前辈嘛。
每个人的故事都有一匹布那么长,我想说的不是比惨,而是怎么凉拌。曾几何时我们都「凡尔赛」过,对别人的「凡尔赛」也非常上头,感觉自己活着就是给伟大的时代抹黑,本以为疫情是最糟糕的,内心盘算着怎么把所有个人失误都推在口罩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锅了。万万没想到反而是疫情之后情况急转直下,经济一路下沉,各种爆雷、倒闭潮、失业潮,然后就是集体迷茫。
那么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当然不全是环境造成的,但是以往的顺势顺境会自动遮蔽掉一些不堪和矛盾,因为人意气风发的时候容错率高,现在不行了,那些负面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兀、显眼,让人无法忍受。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会感到一种别样的轻松,尤其是朋友们都困在烦恼中,更显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是生活本真的样子,家里永远是乱乱的,自己永远是气急败坏的,各种事满头包全部等着你去处理。
这不是矫情,正如你爬山、健身、慢跑很累很累换来的是内心的轻松,你放弃优渥接受挑战得到的是精神的解放。现在是我们都不用那么剑拔弩张争当成功者了,终于可以丧丧的了。
当你扛过最艰难的时刻,才发现自己是真的长本事了,进步了成熟了,不再是那个有车有包便「剪刀手」的小孩子了。
有人说时代的红利都被我们吃完了,那么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不再欣赏梦幻制造梦幻,不用装出吃不完用不完的样子,不用粉墨登场,我们将记住罗翔老师说的:「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
(作者为广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钟二毛的「新南方写作」与其不可承受之「轻」●伍岭
今天我们谈论「新南方写作」,批评家们都有各自的看法。显然,这是当代文学讨论中避不开的话题。什么是「南方」,什么又是新的「南方写作」,它受地域的影响吗?自改革开放以来,「流动的南方」就一直是包容、自由、向外走的姿态,在此经验下的文学创作也自然是开放性的。我一直不把「新南方写作」视为深圳或者广东等的地域性概念,它只是借在这个地域下形成的经验来写某个群体或者人类的际遇。我想以三位深圳作家:钟二毛、蔡东、林棹的作品浅淡「新南方写作」的深圳特色与经验。
本期我们先来聊一聊钟二毛。
近期,钟二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晚安》,这本中短篇小说集一共收录了十篇作品,聚焦城市中产阶层,从职场、购房、育儿、养老等深具社会性的主题切入,观照他们的生存与精神困境。这些主题以及钟二毛通过文学来延展的社会问题是属于南方或者深圳的吗?显然不是,它放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需要关切的,哪怕放之四海,也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时代性与现代性,《晚安》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那么它在「新南方写作」的概念里又是什么呢?
本文重点以同名小说〈晚安〉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晚安〉讲述了一位患有绝症的母亲不堪病痛的折磨,请求自己当刑警的儿子给她一个安乐死。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讲了七个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这七个故事既是母亲对人生的回顾,也是对求死的向往。儿子大毛始终平静地面对随时到来的末日,但他的平静就像他每日为母亲烧开水一样,水在壶里滚烫翻转,咕噜咕噜的低吟,只是悲痛一直被压抑着。壶本身的「冷漠」,折射出在生死抉择面前,在传统孝道的阴影下,无可奈何的坚强。
最后时刻的到来,「(母亲)这一丝笑容,仿佛把过去所有的痛苦都抹掉了。这一丝笑容,似乎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钟二毛是一位在描写上非常细腻的作家,此刻的「从零开始」是读者经历过七天的痛苦挣扎后一同面向「新生」(死亡或告别痛苦)的开始,我们似乎可以平静的接受这一切了,但依旧像壶里的水一样压抑着悲伤。
钟二毛写,「我把母亲抱在沙发上,坐好」,他一直在强调「坐好」这个词,是因为母亲此前因为疼痛只能跪着,但这最后的时刻,要让母亲「坐好」,不仅给予母亲最后的尊严,也是在不断加强自己内心的稳,生死离别之际,要把最好的安宁留给母亲,所以要稳。
钟二毛还设计了没有标签的药瓶子,描写了母亲黑洞洞的嘴,也祈求这些药丸、水啊,都能慢点再慢点进入母亲的体内,这最后的母子时光,是钟二毛定格在文学里难舍之情,也是读者无法言说的告别之痛。
身在深圳的钟二毛和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一样,皆为游子,尽管这篇小说未更多提及游子的心境,但通过与母亲的告别,也完成了对游子的乡愁、亲情与无助的空洞心态的深层且克制的关照。这篇小说名为「晚安」,也是对文本内涵的特别的定义。如果你通读这本小说集,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晚安,在都市里,甚至在南方城市中是习以为常,甚至有些轻盈的短暂告别语及祝福语,但钟二毛将此用于「死亡」的主题上,并统领整本书的主题,更体现了他的特别之处——在描写某个群体的精神困境时,借用了「轻」来反衬生活的「重」,那么〈晚安〉也好,还是集子中的其他作品也好,都在述说人间漂浮下的不可承受之「轻」了。
(作者为《深港书评》主编、文化记者。)
明报特辑部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