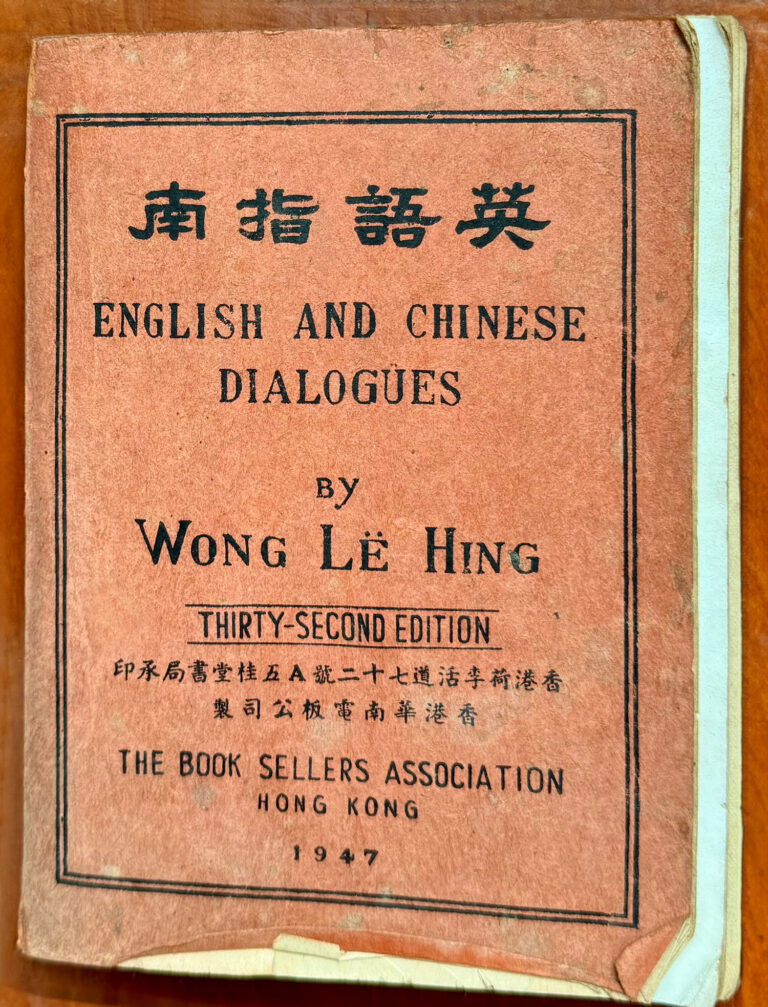太阳正好,赤条条地歪挂在那,又将光端端地散射下来,远处那架黄土山被抹得通红,残阳如血,景物也如血。
黄昏这时,很美。
曾一度变得暗淡如秋的我,独自坐在那痛苦的思想,一直想得头破血流,但最后我到底是一无所获。突然之间一阵暴躁、烦闷的情绪涌上来,以至忍无可忍之时,我将那杯泡得发黑的茶水愤然掷于地上,结果是杯子破碎,茶水寻找到一条路开始默默地流淌,沿路将还没来得及熄灭的烟头哧哧地湮灭。我铁青着脸,走到墙上挂着的那扇巴掌大的镜子前,脸无任何表情,不屑一顾地让目光过去,无限轻视地看自己生自己气的样子,那样子很不让我满意。我深叹一口气:他没来。
昨天是我结婚的日子。早在二十几天前,我就给他前后发了两封邀请信,只是到今天还不见他的影子。我无限伤感,他是不是因为他结婚时我没有去而记恨我了?正当我很悲伤地忐忑不安时,木门开始咚咚震响,有人砸门。我拉开一看正是他!这位自远方而来的老朋友,和我相互间淡然一笑,小屋里便立刻有了一股看得见的暖色调。阳光挤满了整个房间。
这个令人激动的七月,使我顾不得自己的新婚妻子,要和朋友去看山。那山上有太阳——太阳下有一个大水坝,水里又浸着颗太阳,湿漉漉的沉到水底,将水染红了红红的一坝水。情绪在这一瞬间是如此的惬意。我们同时感觉到。
「日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他眯着双眼。
「老婆还好吧?」
他沉默无声。猛然两肘撑地倏地站立起来,将瘦得谁都会可怜的肚皮努力着鼓起来,两手指指。我意会到了他所示的含意,我仿佛看到他老婆肚子里那个活泼的太阳。
「有声音吗?」
「咕咕的。像一管生了锈的法国小号声,是很能让人感动的。」
我呆呆地任意去想像他这时的感觉。
远山上,一位喊山的牧羊汉执把鞭子,在胡乱地漫着没有水分的干巴巴的花儿,声音直勾勾的:
太阳落山一会了,
看不见阿哥的影子;
寻不见阿哥我不走,
我只有这一点本事。
这位朋友斜瞅着那颗太阳,嘴里叼着的烟头忽然一亮,我忽然感觉到离我们很近的太阳也忽然一亮。他的脸是瘦黑了,胡子长得野草一般缠绕了满脸,那两只眼睛却很精亮。我知道他这几年为自己的事费了心了。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冲我嫣然一笑,说:「人受点磨砺也好,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这样的。是吧?」
「是的。」
「喂,哥们儿,咱俩比打水漂吧?看谁打得多,谁多谁这一辈子就有大福。」
他是一个在山沟沟里生长的养子,尝够了人生的艰难,靠自己的能耐上了三年师专回去后,早早地和一个看上他的丫头结婚了。结婚时他满怀信心地叫我去凑凑热闹,结果他这个最引以为是知己的我没去。我知道他不会原谅我的,于是我每天都在忏悔,似一个精神病患者。今天他高高兴兴地突然姗姗来迟,我也大为感动。
小石头片都打出去了,沿平静的水面轻轻地跳跃着前去,如一颗颗小小的串起来的太阳,泛着红光。
「你怎么比不过我了。」他看起来很兴奋,我知道我是有意不好好打,他迷信自己的话。 「你为了让我高兴穷装蒜!生活对我毕竟是严酷的啊,我自己都无法改变,你他妈的能帮我改变?」他恼怒了,揪住我的头发,朝我脸上猛砸一拳。他那双曾吃过苦的手真有分量,我眼前金光四闪。
太阳破碎了,变成了盛开的花,我闭上了眼睛,金光是不闪了,脑袋却不停地「嗡嗡」作响。
他愣着眼坐在一抹土坎上。那太阳是落窝了,余晖却挥洒自如。将流血泼了满山,山便显得很悲伤。
水呈暗了,土黄土黄的像撒了一层黑玉,四周无风吹来,水便寂寞无声静静的。远处的黄土山不黄了,则是一片朦胧的青黛色。我们的心却在剧烈地跳动,黄昏的眼睛看着我们不眨动雾状的睫毛。
「给你说句实话吧,我老婆生孩子时死了,都死了。」他声音呜呜的。
「什么什么什么……」我彻底清醒过来。黄昏仿佛又亮了许多。
远天传来一个尖细的云雀声,声音凄惨得掉泪。这时,我不知所措,安慰全是些空洞无物的东西,他也很不需要我采取这种他一贯认为是虚伪的方式。但在没有任何办法之下,用安慰试探一下吧,总比不试一下的好。我走过去觉得路很长,一直延伸着下去没有尽头。
「哭一场吧……」
我的话音还没散完,他抱住头便委屈地嚎啕大哭,好不凄凉。唉,这个从没掉过眼泪的山汉哟!
黄昏好像又深沉了一截,被捂了眼睛似的,金黄的泪痕贴在天际。哭声终于止了。他沉稳地走到我面前,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对我依旧信任的微笑。我的灵魂在黑暗中狠狠地颤抖了一下。我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重新人生!」他说。
「重新人生!」我说。
两双手在昏暗里紧紧地握在一起,有烫人的热流穿越了我们的躯体,似电若火。眼睛们在这黄昏中闪烁出光亮,闪烁出坚毅。我们看懂了各自的眼睛。
太阳回家了,今天的黄昏是回不来了,但我们深信,太阳明天还会升起。
黄昏的眼睛终于又亮了,而且亮了一大片,闪着璀璨的白光。 (作者为珠海作家。着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中华散文》、《广州文艺》、《雨花》等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