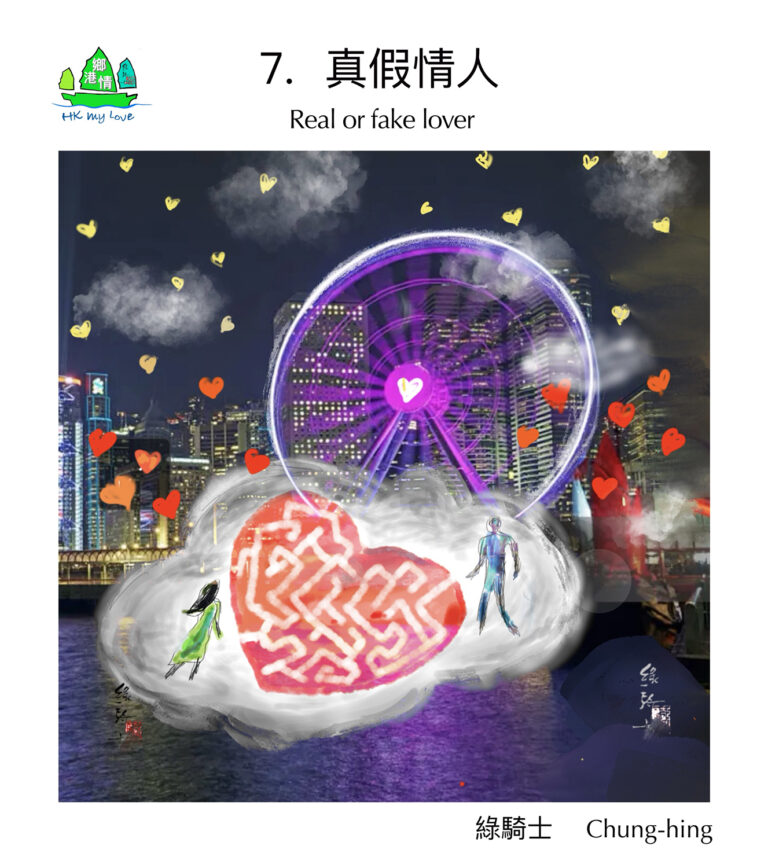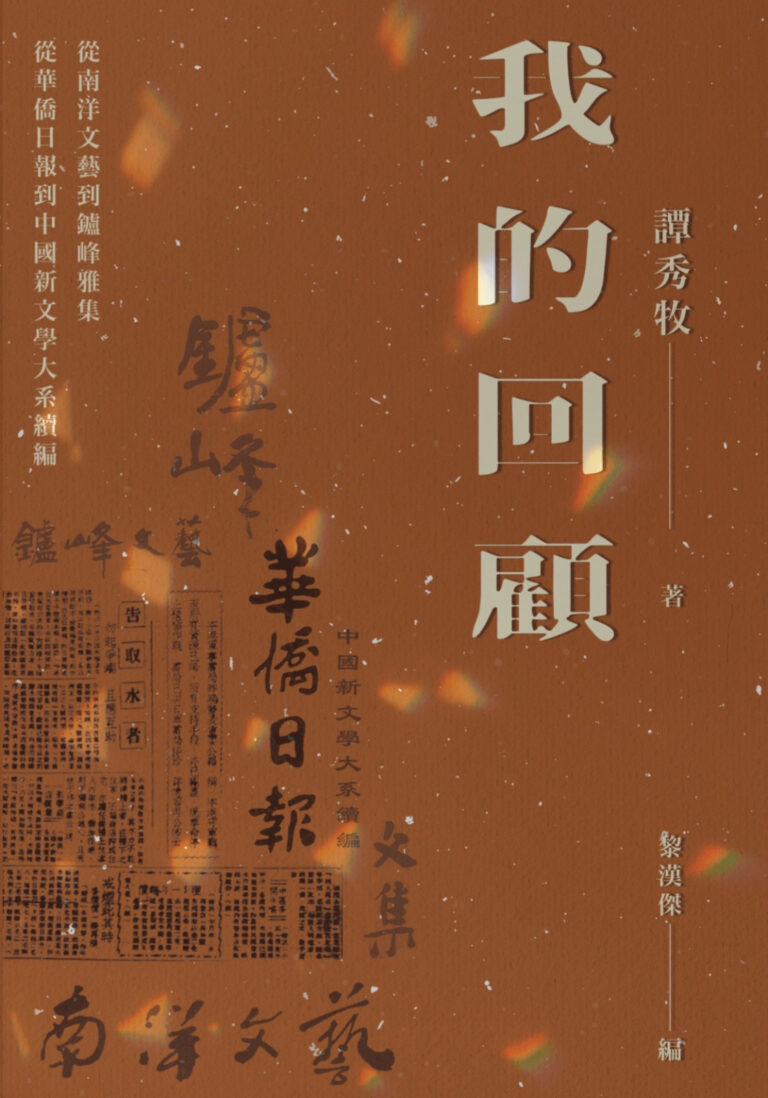编按:作者探讨近年以广州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透过细读林棹、葛亮、魏微等作家的小说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多元叙事手法,描绘广州的城市风貌,揭示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大湾区城市精神。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入推进,「广州叙事」悄然勃兴,期间更是诞生了一批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广州城市题材小说」,如林棹的《潮汐图》、葛亮的《燕食记》、魏微的《烟霞里》、宥予的《撞空》、索耳的《细叔鱿鱼辉》、伍华星的《入刀山》等。这批作品有别于简单的城市地理志,它们凭借多元的叙述形式和崭新的文学观,勾绘出广州乃至整个大湾区城市历史的独特风貌,为当代汉语叙事注入了新鲜活力。
此处所谓「广州城市题材小说」,指以广州为背景、表现广州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及城市变迁等方面的小说创作,这类小说通常会深入挖掘广州地理环境、方言习俗、历史遗迹、经济发展、社会问题等,呈现广州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特征,经典作品有黄谷柳的《虾球传》(一九四七—一九四八)、欧阳山的《三家巷》(一九五九)、章以武的《雅马哈鱼档》(一九八三)等。与既往的同类型题材不同,近年来广州城市题材小说无论在叙述形式、人物塑造,还是对城市风貌的描写上都有了新的变化。
长篇小说方面,林棹的《潮汐图》(二○二一年)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巧妙融合粤语方言,塑造了一只雌性巨蛙在十九世纪的广州、澳门和英国的奇幻旅程。这部小说借画师冯喜之口,对广州城市风貌做了细致描摹,更彰显出一种博物学视野下的城市浮世绘:冯喜成名后在广州靖远街开画肆(这条街坐落在番鬼、洋人、外江佬、广府人混居的十三行一带),他受博物学家H之邀为巨蛙制作博物画,并教画肆的伙计们认博物画中的生灵(五彩蝶蛹、缝叶蚁大巢、万物标本等),也教巨蛙识字(汉字、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冯喜眼中的世界,正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清代广州,寰宇、世界、四海、万国等名词在此并非虚设,而指向东方与西方相遇、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历史时刻,指向「天朝上国」(天下)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前夜。在这个时空中,不同的宇宙观、知识系统碰撞出火花,博物学和博物水彩画,即是一个缩影。
与之相对,葛亮则以「历史小说」为方法,其《燕食记》(二○二一年)由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经历钩沉故事,空间上起于岭南,终于粤港,时间上由辛亥革命至陈炯明治粤到当下约百年间。葛亮由此摸索到一条切近湾区地域文化和精神症候的取径,这番努力在近期的「匠人系列」(如以香港发廊为线索书写世情变迁的《飞发》)和《燕食记》这部全景式叙写广式茶楼兴衰史的长篇里开花结果。 《飞发》结尾,代表香港街坊精神的粤式「飞发」师傅翟玉成与代表海派理发的庄师傅的和解(庄师傅在病房为弥留的翟玉成理发),象征江湖道义,也寓意海派与粤港文化融合的可能——其中,翟玉成与郑好彩夫妻相濡以沫的情节演变为《燕食记》里陈五举与戴凤行的恩爱相助,读来感人至深。可以说,葛亮对情义、道义的书写俨然升华为一种小说诗学。
多维笔触刻画广州风貌
无独有偶,作为「改开年代」的同时代人,魏微的写作总是和时代的幽微变迁「同辐共辏」,这尤其体现在这部以「编年体」形式写就的《烟霞里》(小说最初在《收获》刊发时拟命名为《一个人的编年史》)。小说大开大阖,从田庄的出生(一九七○年)一直写到其猝然逝世(二○一一年),空间上遍及田庄生活过的李庄、清浦、江城和广州,对田庄从村庄(李庄)到县城(清浦、江城)再到城市(广州)的人生轨迹做了一次巡礼和细描。其中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和广州的书写尤其精彩,生动还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珠三角都市风貌,小说也借此将田庄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社会做了巧妙「对接」,使二者「同呼吸、共命运」。
宥予的《撞空》(二○二三年)和我们寻常所见的长篇相距甚远,它拒斥家族叙事,亦非成长小说,不依靠核心事件与冲突矛盾推动情节,更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标。从形式上看,它就像主人公何小河的一份「广漂」生活日志,以第一人称视角,细腻描绘了其工作、生活琐事与心路历程,真实再现了无数外来者在广州这座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体验。尤其富有匠心的片段是小说的「第二部」,它以何小河对前女友陈小港的追忆开篇,继而切入苏铁对彭冬伞的跟踪过程。何小河为了揭开困惑(陈小港为何出现在笔记本里?)决定还原苏铁的跟踪路线。他行走在广州城里,海珠桥、小港路、草房围……商铺、招牌、便利店、食肆、居民楼,街道的面貌、生活其中的人,南方城市的潮湿气候、雨、云、珠江和语言等,被何小河的目光一一扫描,凝固为纸上风景;蒲荔子的长篇新作《虚荣广场》(二○二四年)则将目光对准二十一世纪初广州的作品,其笔下的东山口、杨箕村、广州火车站等地理位置、城市空间,散发着独特的时代「光晕」(aura)。在描绘人物情感和心灵的同时,这部小说对广州城市生活的复杂肌理做了深度透视,它通过叙述层面的「回顾视角」、对「成长小说」模式的拟仿,以及独特的小说语法,写出了人物复杂的情感结构,实现了对「文学广州」的虚构与再造。此外,张欣的《如风似璧》(二○二四)以文学之笔重塑了「民国广州」的城市形象,为广州城市文学竖立起一座重要里程碑。
在中短篇小说方面,陈崇正的《开门》(二○二一年)通过「援非」医生、抗疫志愿者和门锁修理工在封闭空间的相遇,构建了讲述广州故事和中国故事的叙事蓝本;索耳的《细叔鱿鱼辉》(二○二三年)通过描绘上世纪九十年代广漂青年「鱿鱼辉」在歌舞厅反串梅艳芳谋生的经历,展现了一幅鲜活的广州市民生活图景。这部中篇小说从一九九三年写起,横穿二○○三年,被誉为「香港的女儿」的梅艳芳支撑着细叔从青年走向中年。这段精神成长史恰与广州在「漫长的九十年代」的城市史和社会史发展同辐共辏。 「鱿鱼辉」这一形象便是九十年代特定的「文学产物」,它糅合两个原型(在广州宵夜档反串梅艳芳而出名的市井明星「炒螺明」以及自九十年代中期起凭借一支老旧红色风筒闯荡广州烧烤江湖的「风筒辉」),如此鲜明动人,是近年来书写粤地粤人的文学典型;与之可形成对照的,是同样观照九十年代省城(广州)的中篇小说《入刀山》(二○二四):主人公进山探视入院多年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原本只为交送阿嫲去世后留给姐弟二人的微薄遗产,不料自己成为向导,带领三个病人出逃下山(「出山」)。作者伍华星有意避开具体的时间标识,但小说里启用的大量粤方言和细节无不在提醒读者:「我」与从福祉院逃出来的「阿弟」(「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波鞋哥和笑面人游荡之地,即是九十年代工厂林立、高速发展的广州。
文学视角折射湾区精神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之一,其城市文学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与魅力。而广州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更是在当代城市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潮汐图》到《燕食记》,从《烟霞里》到《撞空》,这些广州城市题材小说的创作,既是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是对全球化语境下城市发展的深刻反思。它们通过方言的创造性转化、对城市空间的细腻描写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深入刻画,呈现大湾区城市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融和碰撞。在此意义上,「广州城市题材小说」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成为大湾区城市精神的生动写照。
(作者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广东省作家协会签约文学评论家,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云山青年学者。)
爷爷的枪●王溱
顶楼的房间租金自然便宜些。谁也不愿爬那嘎吱作响的木楼梯,尤其是夜归的时候,每踏一步都能听见楼梯不满的咒骂,楼道壁布满冷峻的眼睛。她安慰自己说高点好,高点视野更广阔,方便看日落,或者看日出,尽管这栋公寓也就五层,还不够格关心太阳的行踪。
「站得高,才能望得远」——这是爷爷说的。
「居高临下方可掌控敌情」——还是爷爷说的。
爷爷说的,她信。小时候她住碉楼,爷爷会把枪挂在碉楼最高一层的靠墙处,以便有什么情况可以快速取下,枪口从墙上的小孔伸出瞄准来意不善的入侵者。她至今还记得木枪托在月光下泛出若有若无的光,那是被人常年摩挲出来的包浆。她也喜欢抚摸那枪托,滑滑的,凉凉的,有时还会把脸贴上去。童年因为这杆枪的存在而充满安全感,即便自始至终她都没见这杆枪响过,一回都没有。据说爷爷的爷爷一枪没开过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据说的,据爷爷说。
城里没有碉楼。这破公寓哪里比得上碉楼?但她还是走到窗前学爷爷居高临下瞪大双眼巡视。远处喧哗的街市和近处稀落的路灯尽收眼底,她却怎么也摸不清「入侵者」的底细。 「入侵者」不是人,是光。光影狡猾且变化多端,一下是圆形的,如手电筒所照,像极了一伙城市猎人在四处搜寻刺激;一下又雪花状闪烁,如同用手机翻拍的黑白无声电影,极有可能下一幕就是数不清的凌乱脚步,某只鞋上还沾着呕吐物;更放肆些的影子会靠近她,几乎是紧贴着她眼皮底下晃,如醉汉摇晃的虚影,避无可避。
她忍住筛豆般颤抖的身体,假装爷爷的枪此刻就在自己手里,把枪口伸出去,瞄准。该朝哪儿瞄准呢?光影没有形状,总在她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又从她意想不到的地方消失。与其说像鬼魅,不如说像来自另一维度的怪物,身手敏捷且能随意变幻,大能填满整间屋子,小能挤进她手指上细狭的伤口。
胡乱瞄了一会儿,她的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这样的「敌人」不像碉楼外的入侵者那样由远至近一步步靠近,即便手上真有枪,又能怎样?
更何况,她没枪。
记忆中的那杆枪随着爷爷的离世不知所踪。
丧讯是昨天阿爸打电话告诉她的,轻描淡写。没别的意思,就是告诉她不必急巴巴赶回来,该办的都在办了,早点入土为安,让她安心留在城里上班不必来回折腾。她自然不会听,心里悄悄琢磨怎样跟老板娘请假成功率更高。跟阿爸有一搭没一搭聊了一会儿,她终于忍不住问起爷爷那杆枪的事,阿爸愕然,说家里哪来的枪。她不甘心,给阿爸描述着枪的模样,还有挂的位置,阿爸打断她的话一口咬定就是没有枪,说那是老黄历的事儿了,家里早就没有枪。
没有枪?
阿爸说得很笃定,没有枪。
难怪眼前这些怪物如此肆无忌惮!她坐下,它就在墙上与她对峙,目光有些不满,甚至带着嫌弃,让她想起今天开口请假时老板娘看她的眼神;她站起时,它就往她背后跑,速度很快,总能在她回头的那一瞬间消失不见,让她心里空落落完全没底;浴室吊着的灯泡也被它收买了,一直摇晃,一闪一闪,隐约还带着粗壮的喘气声。若怪物张大嘴把她一口吞了倒安宁,它偏不,一遍遍强迫她反刍今晚不堪的经历。
今儿回家确实晚。她答应老板娘把未来几天的工作都做了才得以顺利请假。午饭啃了包饼干,晚饭也没工夫吃,满脑子都是电脑里的数据,路走得踉踉跄跄,意识跟不上脚步。大意了,真的大意了,她竟忘了避开死角,避开阴仄的小巷。
那一群醉汉就在转角处,动静是有的,她竟半点没有提前发现,待转身欲往回走时已被人拉住,呼啦被围在了中间。
她低声求饶,颤抖的声音瞬间被醉汉们肆无忌惮的笑淹没。她便大声呼救,更大声的,是不知谁手中的酒瓶「啪啦」碎一地的声音。
昏黄的街灯根本指望不上,它们只会把醉汉的身影与破碎的月光混在一起摇晃,地上的影子杂乱无章,空气中弥漫着呕吐物的酸味。她下意识双手抱胸往地上蹲,被一只黏糊糊的大手硬拉起来,挣扎中她的手被什么划了一下,也不知流血没,钻心般地疼。
「住手!」
「放开那个女孩!」
「我报警啦!」
「还不快滚?!」
不远处传来响亮的几声喝。有路人经过,人数还不少。醉汉们没有得逞。谢天谢地。
该死的光影们却得逞了,尾随她回了公寓。她好累,踏上木楼梯的步伐如同出殡般沉重,死一般寂静的房间里仿佛有哀乐奏响。记忆被凌乱的脚和交错的身影搅得支离破碎,她蜷缩在床上,忆不起任何一张醉汉的脸,甚至搞不清那些身影的具体数量,如同一只忘记弓长什么样的惊弓之鸟,独自在这小小的房间里瑟瑟发抖。
她决定开着灯睡,大大小小开了近十盏灯。足够多的光源就能稀释那些可怕的光影,这是无影灯的原理。方法没问题,但这破公寓老旧的电路出了问题,才开一会儿就跳闸了。

(资料图片)
啪!一片漆黑。
所幸窗外还挂着一轮不甚圆的明月,勉强把满室漆黑变成稀释过的浅黑。她揉着眼睛好让眼睛快点适应,揉着揉着突然瞪大了双眼。
枪!一杆枪!
餐桌有个长长的影子清晰可见,形状像极了爷爷那杆枪!
她循着月光来的方向找,很快在窗台上找到了这杆「枪」的出处——一块从手指上扯下来的创可贴。创可贴是今晚救了她的那帮人里面一个可爱的圆脸女孩给她贴上的。女孩很细心,先拿纯净水洗伤口,用嘴吹干,这才小心翼翼给她贴上,离开前还不忘轻轻摸摸她的脸,给她安慰。洗澡时创可贴打湿了,她便扯下来随手放在窗台上,月光大概是受了谁的嘱托,硬是把影子拉成了枪的形状。
「怪物」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她颤抖着伸出手去摸那杆「枪」,没错,滑滑的,凉凉的,忍不住把脸贴了上去。
「爷爷,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憋了一晚的她终于大声哭出来,哭得声嘶力竭,犹如灵堂前的孝女。
(作者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岭南偶遇》、《同一片海》、《第一缕光》及短篇小说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