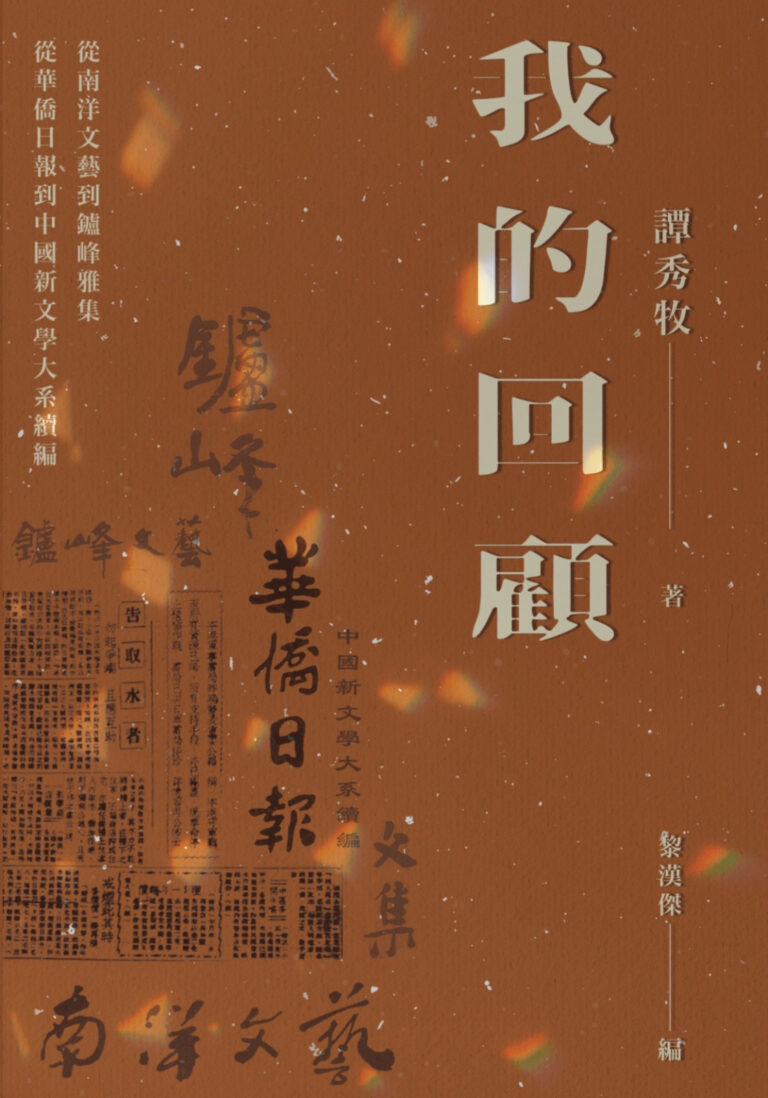编按:「八十年后的今天,我轻轻抚过父母留下的文稿旧物。墨迹虽已泛黄,但字里行间的热血依然滚烫。这些文字不仅是家族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作者忆述父母周钢鸣、黄庆云在烽火岁月分别以战地报导、爱国诗作及抗日歌词唤起全民一致抗敌,以文字传颂那时代的赤子之心。
抗日战争后的八十年光阴流转,如今我们又迎来了一个伟大的胜利纪念日。这些天我埋首整理父母亲的抗战纪念旧物,其中有母亲黄庆云在抗战七十年纪念时国家给她颁发的纪念勋章,还有父亲周钢鸣写下的《救亡进行曲》歌词。在晨光中仿佛被镀上一层金边,将我带回父母用青春书写家国大义的烽火年代。
父亲周钢鸣那年二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毅然留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用笔墨作为抗敌的武器。我常听他说起创作《救亡进行曲》的那个夜晚,闸北的炮声隐约可闻,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与作曲家孙慎等进步青年挤在工人夜校里,字斟句酌地推敲歌词歌曲。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
激奋人心的悲壮旋律就此诞生,并且很快响彻了大江南北,成为无数抗日志士的精神号角。 《救亡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同为抗战歌曲的姊妹篇,激荡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说那是民族精神的最强音,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用血肉谱写的抗战史诗。
父亲最难忘的是前往四行仓库采访八百壮士的经历。苏州河两岸硝烟弥漫,他冒着流弹匍匐前进,眼见年轻士兵们用身体护旗的场景。归来后彻夜未眠写就的战地通讯,字里行间都是热泪与热血,这些报道后来成为研究淞沪会战的重要史料。
父亲后来又和《义勇军进行曲》(如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田汉先生等并肩战斗,辗转在各地的抗日前线,并跟随茅盾先生来到香港,写下了对战地记者工作指导书籍《怎样写报告文学》,成为当时革命根据地延安鲁迅文学院的参考教材。
与此同时,在南中国的香港,十七岁的母亲黄庆云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参与救亡。她代表香港学生联合会,向即将北上的医疗救援队赠送战旗。母亲曾告诉我,那天维多利亚港细雨霏霏,她将绣着「戮力同心」的锦旗交到队长手中时,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更难得的是母亲在《探海灯》报同时发表抗日诗作:
英雄奋身思报国,浴血挥戈杀倭贼。
鏖兵春夏且秋冬,转战东南复西北。
枪林弹雨拼冲锋,救死扶伤日不给。
更有粤人言不识,创痛向谁诉胸臆。
语言隔膜难相传,念此贱躯痛何极。
以身许国身非我,血肉之躯当炮火。
呻吟辗转穷呼天,狂呓犹将暴敌破。
顽疮不治成待毙,恒痛相煎血为泪。
捷报西风指顾间,孰令壮士身先死。
白云低低不敢飞,此日我军成玉碎。
七尺昂藏耻瓦全,奋起青年救国团。
振臂一呼群众起,救护队成何可观。
明日首途赴前线,愈我伤军军复战。
灭此朝食履扶桑,时日曷丧予及见。
买丝绣得旗赠君,珍重成仁一片心。
故国历历山河在,疮痍满目待君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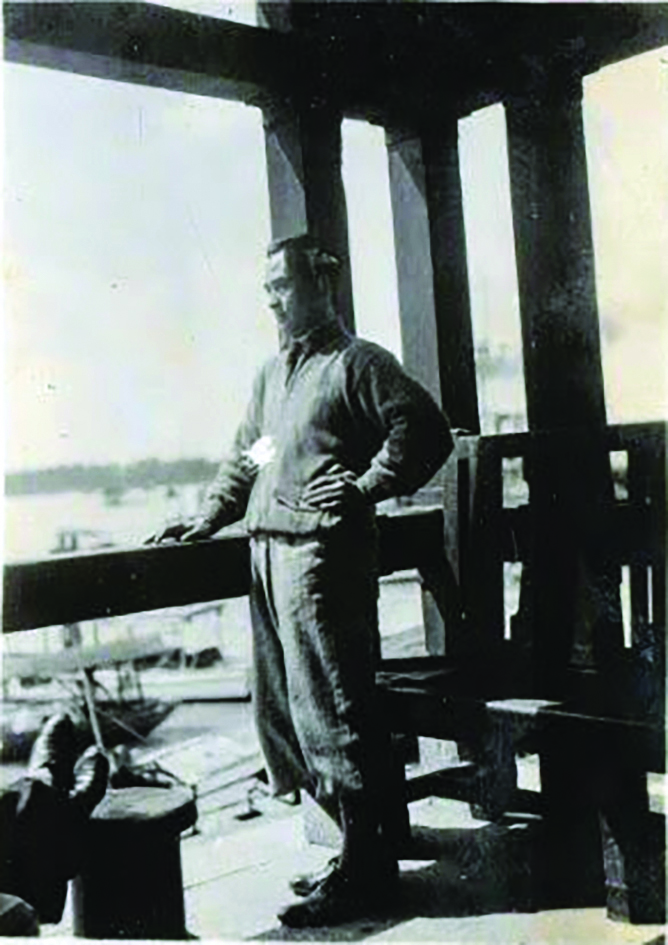
那些铿锵诗句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英雄奋身思报国,浴血挥戈杀倭贼」——这是对前线将士的礼赞;「枪林弹雨拼冲锋,救死扶伤日不给」——这是对战地医护的致敬。尤其「语言隔膜难相传」一段,真实记录了粤籍士兵在异地作战的困境,展现母亲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
「以身许国身非我,血肉之躯当炮火」这两句,恰是父母那代人的真实写照。他们本都是文弱书生,却在民族存亡之际爆发出惊人力量。父亲用歌词唤醒民众,母亲用诗句鼓舞士气,他们以笔为枪,在文化战线上筑起新的长城。
记得十年前接到广东作家协会转来一位母亲当年的小读者来信,里面附有这首诗的剪报,但其中有些字迹不清楚,当时九十七岁的母亲即时拿出笔来补填上,我为她的记忆力深感震惊,十七岁和九十七岁,这是多么大的跨度呀,但母亲的爱国抗战情怀始终未曾改变!母亲告诉我,那支医疗队多数人再未返回香港。母亲说,她后来总想起那些年轻的面容,一直难以忘怀。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轻轻抚过父母留下的文稿旧物。墨迹虽已泛黄,但字里行间的热血依然滚烫。这些文字不仅是家族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它告诉我们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值得珍惜,而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精神,应该代代相传。
夕阳西下,我逐字逐句写此文,纪念所有为抗战奉献青春的人,他们的故事应当永远被传唱——在淞沪大地,在香港之畔,在每一个向往和平的心灵深处。
(本文图片由周蜜蜜提供。作者为香港作家、儿童文学作家、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
泣血岁月香港情 ●何佳霖
抗战组诗
一
当造物主闭上爱的窗户
一群铁鸟失去了血性的温良
这个被觊觎的港口海湾
一个肥沃的旧日渔村
一个个列强垂涎欲滴的香港
此时变成了孤岛
那些人是谁?那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没有人听见他们的话,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话
落日像哭肿的眼睛透出冰冷的寒气
孤儿寡妇在承受莫须有的灾难
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
黑色的圣诞节,
时速在狂奔
子弹炸药在狂奔,
侵略中国土地的日军铁蹄在狂奔
火海以秒计漫过东西交汇的人类文明
断简残篇说不完国恨家仇
一些人把胸膛顶向尖刀留下丹心碧血
一些人壮志未泯捍卫脚下的土地山河
铁鞭拷打也榨不出同志的下落
谁说书生无用?你看周树人、柳亚子、茅盾、邹韬奋……
他们用生命拯救生命,以灵魂点亮灵魂
三
日子在沦陷,卢沟桥在沦陷
上海在沦陷,南京在沦陷
蒋委员长在沦陷,墙上的万岁在沦陷
广州在沦陷,启德机场上空在沦陷
香港在沦陷,世界在沦陷
打着「东亚共荣」的侵略者在沦陷
港督在沦陷,天皇在沦陷
不平等条约在沦陷,野心勃勃的战犯在沦陷
这是谁造的因,这是谁造的果
当中国人民自己站起来,当世界人民一起站起来
我们的沦陷就是你们的沦陷
烽火南溟香江抗战
一九四一,这一年的冬雨格外阴冷,云层灰暗,重重压在香港太平山顶,仿佛老天也屏住了呼吸,任由人间灾难蔓延开去。十二月的风本该带来圣诞的欢愉,但中国大地,山河已破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半壁江山沦陷于敌人之手。岭南大地在敌我拉锯中艰难喘息。香港虽暂得偏安,却早成惊弓之鸟。
十二月八日,日军战机群如蝗虫般扑向启德机场,爆炸声震碎香港往日的相对宁静。侵略野心已无可置疑,本来还抱有幻想的港英政府节节败退。日军自东西两路越过深圳河南侵,其中一路入上水、粉岭,直捣大埔、沙田;短短半个月内便登陆港岛,穿过北角、太古等地,迅速建立滩头阵地,香港已变成任人鱼肉的城市。十八天后,半岛酒店楼顶降下米字旗,港督宣布投降。这是黑色的圣诞夜,南来的知识分子们藏起文稿,民主人士烧毁往日的一些信件,教授们将一些典籍埋进菜园,心里预感香港也不能幸免于这一浩劫。但他们,在承受国难的同时,仍怀希望。中国人绝不能就这样屈服,绝不能等死。他们心中有一腔热血,更有一盘对侵略者的新帐旧帐深深铭记。
战火连天的时代,也造就英雄辈出。著名文化人邹韬奋在此前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奔走,推动了各地的爱国救亡运动。他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再次回到香港后,仍然坚持办刊,邀请茅盾和夏衍作主笔,他亲自负责撰写社论。他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月发行量达十万份之多,得到广大读者回应。在他们的推动下,海内外华人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东江纵队第五大队的部分游击队员奉命插进「新界」。那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新界,土匪横行。他们配着长枪或短枪,大多数是英军溃败遗下的武器。村民不仅要面对日军,还要防范土匪的侵犯。武工队的指战员深感情况严重,当务之急就是团结群众,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维持治安。西贡昂窝村客家妇女凌娘就是巾帼英雄的典范,她不但慷慨借出自己家房屋给港九大队军需处办公,还鼓励两个儿子参加游击工作。她在家曾救治过病危的游击队员。她好比现代版的穆桂英,被誉为游击队的母亲。在苦难的岁月,总有一些心怀家国的人舍身成仁,同时为子孙后代谱写了永恒的光荣史。
南涌的罗屋是一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庄,罗汝澄的家乡,他生长在一个华侨家庭,在当地颇有名望。抗战初期,兄弟三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战火燃烧他的家乡,兄弟俩带头把家里防匪的步枪、猎枪、信号枪都献出,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组织群众自卫武装。

营救工作如火如荼,新界郊外元朗客家围屋,十七岁的游击队员阿彩,用柴刀劈开最后一只樟木箱。这个曾经只会刺绣的蜑家女,此刻把祖传的嫁妆箱改造成担架。她将一件靛蓝布衫递给邹韬奋,自己腰间却别上了两颗土制手榴弹。邹韬奋,这位长期为民族的进步废寝忘食的文化战士,以坚定如炬的目光给这个稚气未脱的青年增加了信心。这批已深入香港基层的革命人士,他们离不开这里的村民,一饭一粥,一草一木,甚至一动一静,都与他们的救亡计划息息相关。
人口嘈杂,楼层昏暗的深水埗,一座唐楼的天台上,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算盘打得劈啪作响。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广东商人」,账簿里记着特殊的「生意」:三十二担药材等于营救茅盾的船资;五十匹阴丹士林布等于二十张假身份证;而昨天那口柏木棺材里,装的其实是发报机零件。他扶眼镜的左手小指缺了半截——去年在启德机场接应英国情报官时被铁丝网刮去的。他发誓,只要身还在,必须作战到底。
根据部署,廖承志、乔冠华和连贯等分别行动,通知住在九龙和香港岛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立即搬家隐蔽。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扮演各种身份,想尽各种办法,安排交通员到「棺材铺」老林那里:明日几点送七口「寿材」去西贡,要配「长生板」,接受任务的人心领神会,他们知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每个参加行动的人都要读懂各种行动暗号,七位文化名人将伪装成送葬队伍,而「长生板」特指装有夹层的渔船,护送任务由武工队负责。这天黄冠芳打扮成商人,他买了几份敬神用的香烛、供品,见到廖承志等人后,每人一份拿在手上,扮作香客混进九龙城。当晚,廖承志等一行四人偷渡大鹏湾。他们既要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的搜捕,又要提防土匪抢劫。在夜幕的掩护下,凌晨三点顺利到达沙渔涌。武工队顺利完成了首次护送任务。他们的智慧和胆量已经超越了生死。正如后来移居香港的张爱玲所言:「香港是一座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乱世里的人,就像大海里的珍珠贝,被迫用痛苦孕育出绝美的光华。」香江两岸的灯火璀璨,恰是那代人以生命点燃的永恒火焰,他们敢以生命拯救生命,以青春交换青春。这就是民族气节与人性光辉。
参与这段艰苦救亡行动的见证者——九十三岁抗战老战士林珍老奶奶拄着拐杖说:「国家有难,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事外。」文化名流、民主人士、国际盟友在群众掩护下悄然北撤。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里泛黄的报纸,西贡抗日纪念碑前的鲜花,老奶奶哼唱的战时童谣——都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每当维港升起节日烟花,我们应当记得:有些光芒,穿越八十余年时空依然炽热;有些坚守,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随着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本文图画由庄嘉禾提供。何佳霖为香港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