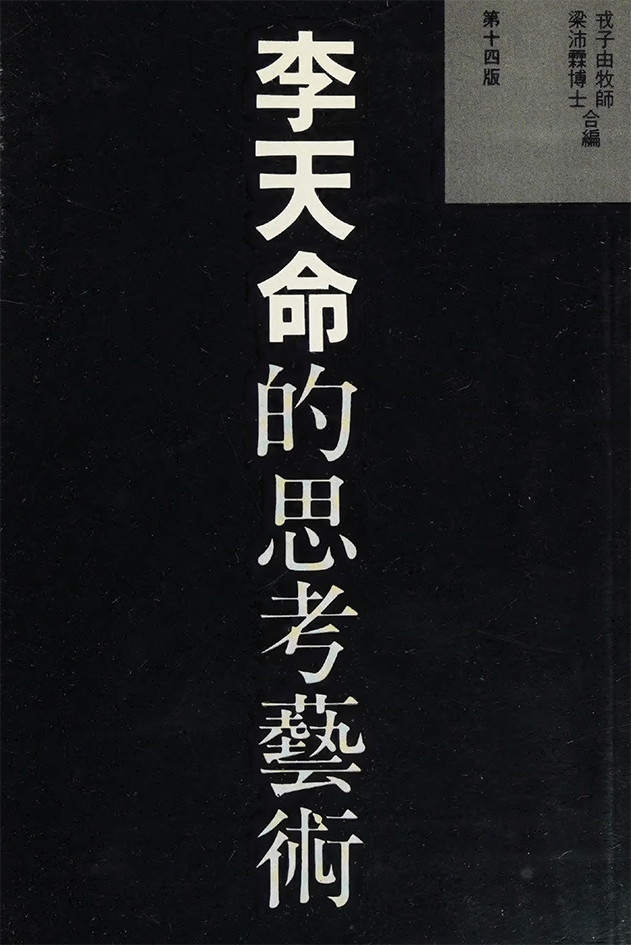编按:著名学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刘剑梅推出新著Chinese Thirdspace: The Paradox of Moderate Politics,1946-2020,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两极之间开辟出新的空间,以实现更大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多元化。这本跨学科著作内容广泛、理论丰富,展现了第三空间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哲学、文学、美学、艺术和电影领域中的关键作用。就此,本版特约记者近月与刘教授进行了笔访,细谈「第三空间」的脉络与意义,并就一些见解作深入剖析。本版主编潘耀明同时细析从霍米.巴巴的理论,到金庸「有容乃大」的实践,再到刘再复「第三空间」的期许,这条清晰地指向同一种价值追求的脉络。
试谈「第三空间」与「中性文化价值」 ●潘耀明
当哈佛学者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遇上刘剑梅教授笔下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套学术话语,更是一种在高度极化世界中生存的智慧。所谓「第三空间」,并非一个物理地点,而是一个思想的「间隙性场域」。它拒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拥抱混杂、协商与动态生成,旨在超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博弈,开辟一个容纳异质思想的公共领域。
刘剑梅教授在其著作中,将金庸先生定位为「更偏向传统价值」,与「第三空间」不尽一致。然而,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视角解读:金庸先生作为《明报月刊》的创办人,其所秉持的「有容乃大」办刊方针,恰恰是「第三空间」精神在公共领域的成功实践。
「有容乃大」——这份胸襟与气度,正是「第三空间」的核心。它要求超越党同伐异的狭隘,在左右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坚持独立发声,容纳不同声音的对话。当年的《明报月刊》,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一个状态、开放的言论场域,它力求客观、理性,在非黑即白的对立中,寻找一种包容的「兼存」逻辑。这并非放弃立场的「骑墙」,而是深知真理愈辩愈明,须在复杂与矛盾中把握平衡的智慧。这也正是本人主编《明报月刊》时所强调的「文化中性价值」,此与李泽厚先生所揭橥的「度」、与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哲学,一脉相承。
「文化中性价值」,其精神内核正与此「第三空间」及「有容乃大」的理念深度契合。要知道,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不应是任何单一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我们致力于打造的,正是一个开放的思想平台。在这里,我们鼓励来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观点的声音进行建设性的碰撞;我们推崇的并非空洞的「价值中立」,而是对多元价值的尊重、理解与包容。从霍米.巴巴的理论,到金庸「有容乃大」的实践,再到刘再复先生「『第三空间』越广,社会就越和平、自由和多元」的期许,这条脉络清晰地指向同一种价值追求。在今日这个资讯爆炸、观点撕裂的时代,守护并拓展这片思想的「第三空间」,是一家具有坚定理念的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中流砥柱」不容推却的使命。
(作者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明报月刊》荣誉总编辑、本版主编。)
谈Chinese Thirdspace——专访刘剑梅教授●李浩荣访问及整理
李浩荣(以下简称「李」):大作Chinese Thirdspace: The Paradox of Moderate Politics,1946-2020(下称Chinese Thirdspace)主要以「第三空间」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思想之间的关系。第三空间这概念由哈佛大学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教授提出,能请您为读者谈谈这概念在学界的影响吗?第三空间跟乌托邦、异托邦等概念有什么异同?
刘剑梅(以下简称「刘」):霍米.巴巴提出「第三空间」是文化意义协商的「间隙性场域」,挑战了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如殖民者/被殖民者、自我/他者)。这种强调「混杂性」(hybridity)和「暧昧性」(ambivalence)的观点,推动后殖民研究从「抵抗/压迫」的二元对立的僵化框架,转向对文化翻译过程中动态权力关系的分析。当然也有学者批评他的「第三空间」理论忽略了殖民经济剥削、阶级不平等、资源分配等物质现实,将抵抗简化为符号层面的「戏拟」(mimicry),由此淡化真实暴力结构。

可以说,第三空间、乌托邦、异托邦都涉及对「他性空间」(other spaces)的想像,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乌托邦是「不存在之地」(no-place),作为完美社会的抽象蓝图,具有封闭性和静态特质。异托邦则关注「真实存在的另类空间」,如傅柯举例的博物馆、监狱、花园等。相比之下,「第三空间」则强调现实中文化碰撞产生的开放性和动态的生成过程。
虽然「中国第三空间」与霍米.巴巴和爱德华.索亚的意图相呼应,旨在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转向更包容的「两者兼具」逻辑,但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现代语境。语境不同,内涵就不同。什么是「中国第三空间」呢?我用书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它是个体的生存空间;是容纳异质思想的公共领域;是宽容与和谐的生活哲学;是平衡自由与平等的第三条政治路径;是调解人类纷争的务实方法;是既非乌托邦也非反乌托邦的温和异托邦;是一个反对直线性的进步观和因果关系的独特场域;或是一个抵抗政治控制、催生跨媒介探索的审美空间。」处于「第三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常左右不讨好,既不受政府的支持,也常常被「反抗团体」的讽刺与排斥,但是他们努力开辟「价值中立」的「第三空间」,因为正如刘再复所说的:「『第三空间』越广,社会就越和平、自由和多元。」
自由主义「第三空间」
李:书中您多次提到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和儒家的中庸、龙树菩萨中论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思想似乎特别适合第三空间的萌发,但事实上,中国的传统社会从不曾产生第三空间。您如何看待这种落差呢?
刘:我在Chinese Thirdspace的这本新书中,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包括道家的阴阳辩证法、老庄精神、龙树菩萨中论,禅宗的不二法门,以及儒家的中庸之道等。这些中国哲学智慧,强调宽容、和谐与平衡,以及悖论的互补关系,我借此来批判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西方的传统形式逻辑(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牛顿的哲学所体现的)主要基于非此即彼的逻辑,或者黑格尔的逻辑还是强调正反合,限制了其把握悖论复杂性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不把两端对立看成一个必须争斗和彼此互相并吞的现象,而是把矛盾和对立的双方看成是可以互补的兼具并存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确实特别适合「第三空间」的萌芽,所以我不同意你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不曾产生过「第三空间」的论点。其实张东荪就把士大夫阶层看成代表「第三空间」的第三种人。虽然他的这一看法有点理想化的色彩,可是他把士大夫阶层看作社会的「中流砥柱」,在社会上发清议、做辩论,把社会内的「清明之气」召唤起来,不仅主持正义,而且疏通统治阶级和大众。他甚至把「士」看成类似英国立宪史上的创立议会,起到「自下而上的防腐作用」。不过,他感慨,可惜中国的士阶层进入现代社会后,没有得势,没有像西方中产阶级,得益于工商业的发达和人权革命,开辟了社会上真正的「第三空间」。
李:书的前言提到,五四健将如鲁迅、郭沫若、陈独秀等人,对于走第三路线的知识分子,不乏攻击,间接打击了第三空间在中国的经营。这三人都可视为左派的代表,那五四时期右派的知识分子是否对第三空间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
刘:如何定义五四时期的右派知识分子呢?谁属于「右派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应该可以定义为右派知识分子吧。自五四文化运动以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被「非此即彼」的思维牢牢控制,总是处于斗争的状态,互不相容,所以我不认为五四时期右派的知识分子对「第三空间」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
属于「第三空间」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坚守独立不移的立场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激烈冲突。其实认同「第三空间」的民国知识分子很多,比如鲁迅所批判的「第三种人」,如苏汶、胡秋原,新感觉派的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无党无派的周作人、林语堂、沉从文、朱光潜,四十年代提出「中间路线」的张君劢、张东荪等。即使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如顾准,中间偏右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都崇尚自由主义,一样属于「第三空间」的宽广地带。
李:书中虽然没有为李泽厚设专章,但几乎每一章均见到李泽厚的名字。请谈谈李泽厚的思想与第三空间这概念契合之处?
刘:李泽厚先生所提出的「度」被我归类为「第三空间」的重要范畴之一。 「度」就是讲究分寸,恰到好处。掌握「度」,就是掌握平衡,如同技术和艺术,跟中国思想强调的「中」、「和」、「巧」、「调」一样。 「度」的主体在不同的时空条件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如果想做到「巧到好处」,一定要结合中国思想中的「阴阳互补」、「和而不同」等智慧。可以说,「度」不仅与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实用理性」的概念相关,也是一种「立美」。 「度」让人要懂得把握像钟摆一样的平衡,不让社会走向两极对立的极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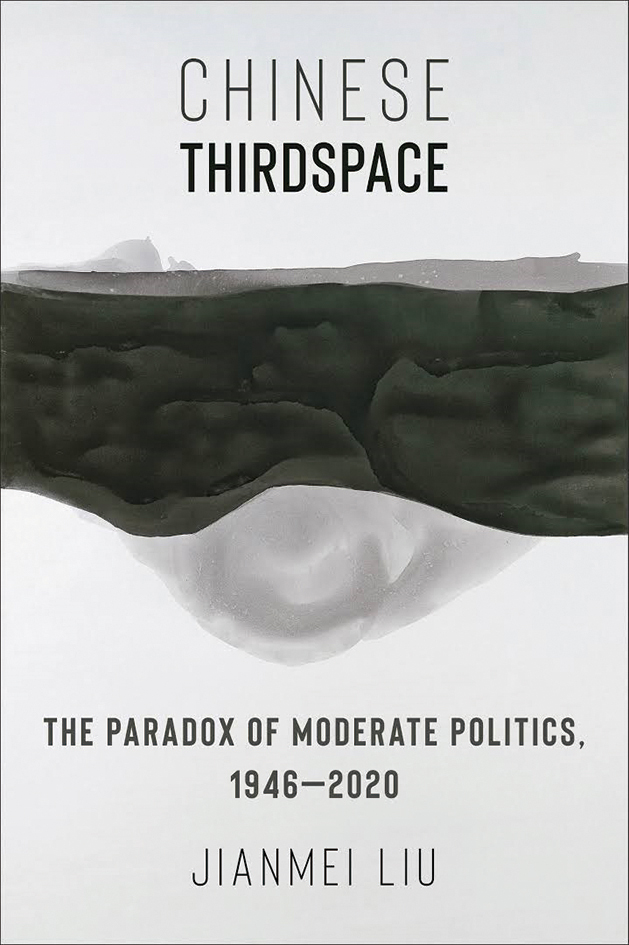
文艺在「第三空间」才获真正独立自由
李:论刘再复那一章提到,刘再复对于第三空间的构想,是独立于霍米.巴巴的理论,异曲而同工。请问刘再复的第三空间之理论,其思想的演化过程是如何的呢?
刘:一九八九年我父亲刘再复到了海外,他面临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问题。因为他不想被绑架在任何两极对立的「战车」上,只想专心做文学研究,所以提出「第三空间」的范畴,即「在社会产生争执两极对立时,两极之外留给个人自由活动的生存空间」。第三空间不仅包括不受外界压制和挤压的私人空间,也包括价值中立的公众空间;既接近中国的隐逸文化和文学的内涵,也接近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中国的语境下,「第三空间」和「第三种人」都没有生存的权利和保障,常常被贬低和排斥,但是我父亲认为隐逸文学和消极自由表面上是柔和无争,内里却有守卫自由的拒绝黑暗政治的力量。在政治层面上,「第三空间」立足于两极对立的中间地带,具有宽广的包容万象的精神,既允许个人回到「自己的园地」,也鼓励价值中立的各种公共空间;在哲学层面上,「第三空间」建立在中道智慧和禅宗的「不二法门」的基础上,打通真谛和俗谛,对天地间多元的生命和情怀都包容和理解;在文学层面上,我父亲认为,文学和艺术只有在「第三空间」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才有更多真正的创新,才不会沦为政治或商品社会的奴隶。
李:论金庸那一章,开首引用了一封金庸致刘再复的信件。附录如下:
再复兄,小梅,
读了「第三空间」一文,甚有同感。拙作《笑傲江湖》中刘正风欲「金盆洗手」,即争取第三空间之悲剧,惜正派大领袖不准,杀其全家,且逼其小儿子批斗父亲。陈家洛归隐回疆,袁承志远赴海外,张无忌不做教主,皆韦小宝「老子不干了」之意也。你们两位基本上已找到第三空间,殊可庆贺。
金庸谨启
能请您谈谈这封信的背景吗?
刘:二○○一年,我父亲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寻求生存的「第三空间」〉,金庸先生读到了,马上写信给我父亲,表示他特别认同,而且他在他的小说中一直都试图表现「第三空间」。他是我父亲多年的好友,两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开辟「第三空间」。不过他当时还不愿意公开此信,担心被左右两派攻击。直到他去世之后,我父亲才将此信收录在他的书中。
李:比较论金庸与论殷海光这两章,便会发现金、殷两人在第三空间里,各有不同的取态。如殷海光主张没有颜色的思想,金庸较倾向儒家的中庸之道,这两者是否属于不同的哲学进路?
刘:殷海光先生早年曾经反对共产党,到了台湾后,除了继续这意识形态以外,他开始尖锐地批判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最终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永远保持独立不移的姿态,不被任何政党以及政党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他的「无颜色的思想」就是主张要客观地谈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情绪化,用暴力语言把对方打倒。总体而言,殷海光先生比较偏向西方的自由主义,他受到穆勒、海耶克、以赛亚.伯林、罗素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颇深。相比之下,金庸对中国的儒释道思想皆有研究,他的小说人物实际上承载了儒释道的文化精神。
「第三空间」的脉络
李:对于新儒家,殷海光甚不以为然。根据您的研究,新儒家的思想跟第三空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另据您所知,李泽厚与刘再复对新儒家的取态如何?
刘:新儒家如徐复观先生也属于「第三空间」的知识分子。一九五七年,他跟殷海光有过关于民本和民主问题的争论。其实两个人从中西文化不同的角度来发展民主自由。徐复观先生认为,民主自由在中国生根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可是,殷海光先生一直都以「五四的儿子」自任,对中国传统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尤其当时国民党利用「复古主义」对自由主义进行大围剿,殷海光认为复古主义和现实权力结合,让民主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所以他对徐复观等的新儒家立场不以为然。李泽厚先生自认为是「新儒家」,刘再复则更接受禅宗的思想。
李:Chinese Thirdspace以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论述对象,如果我们追溯古典文学的大传统,能否梳理出一条第三空间的脉络来呢?如《庄子》、陶渊明、《红楼梦》这一脉络。
刘:刘再复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其实梳理了《庄子》、陶渊明、《红楼梦》这一脉络。他认为这一古典文学脉络,重视自然、个体、自由,跟他所定义的「第三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他在出国前的「第一人生」中,比较倾向接受儒家的入世的思想,积极参与改革,但是他在出国后的「第二人生」,则转而拥抱《庄子》、陶渊明、《红楼梦》这一脉络,选择以「第三空间」作为他的立足之地。
(本文图片由李浩荣提供。访问及整理者为本版特约记者、香港作家联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