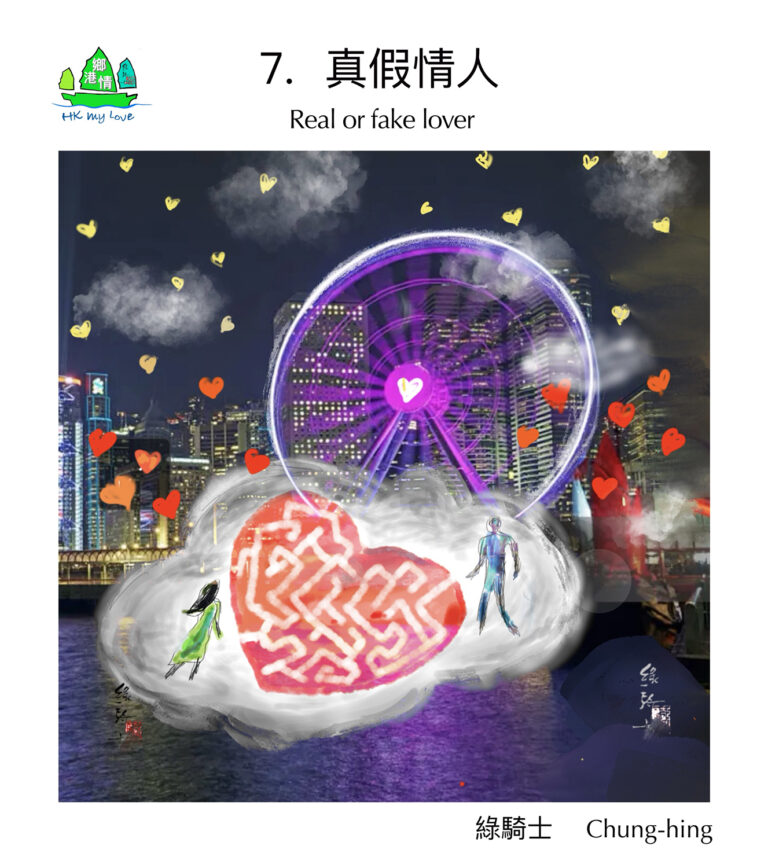编按:近年大湾区发展备受瞩目,新界西正是其重要一环,屯门、元朗及天水围各具特色风貌。岭南大学中文系各体文类习作课程学生以此为题作了一系列创作,描绘新界西的城市变迁与风土人情。本版特精选数篇学生作品刊载,并配以课程导师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师陈伟中博士评语。习作或见青涩,然观察细腻,感情真挚,足见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怀。
石阶垂絮时 ●黄子璇 中文系二年级
青铜色的黎明
刺入羊城的褶皱
你缱绻在珠江咸涩的潮音里
在光绪年的冻土下
倔强,翻身
而我
由珠江的纹路抚育
听江水轻吟你往昔的足迹
从石牌坊书页沙沙
到仙人庙晨钟袅袅
轻轻
在我耳边回荡
在香港的季风里转身
你已是石阶上的古榕
我也蜕成木棉的飘絮
缘份将羊城的铜绿
焊入你褪色的指纹
论文……
汇报! ! !
Deadline——
游标在午夜抽搐
键盘捶打黑铁的寂静
图书馆的太阳
抚平瞳孔里的废墟
在你镌刻沧桑的年轮里
我开始锻造自己的史诗:
银河垂落于笔尖
如同夜空的细语
将未叙的岭南
淬进砚底……
导师陈伟中评语:此诗以岭南大学与广州的历史渊源为背景,透过时空交错的意象(如珠江、石牌坊、仙人庙)建构个人与学校的记忆连结。意象以「青铜色黎明」「光绪年冻土」等意象,将个体成长嵌入岭南历史脉络;结尾突转至「Deadline」「键盘捶打」,在传统与现代张力中探讨学术压力与精神传承的关系。创新尝试:将地理历史意象(铜绿、榕树)与数位时代符号(游标、键盘)并置,形成陌生化对比。
迷失铁路 ●李健诚 中文系二年级
点滴沿耳机线注射进大脑
玻璃月台记录着沉溺者的轮廓
指头反覆摩擦
直到晨昏线缝起眼睑叮当——
离开车厢
春风隔开天桥上的冲突
吹拂麻雀的鸣歌
萦绕孩子们的天真与幼稚
韶光轻吻少年的羽翼
绕行雨后轩的殷红年轮
想追捕铁灰猫尾
晃过一圈,两圈,三圈……
四年刮痕
铬在玻璃表面上
轨道在角膜内飘散成
彩虹色迷雾
闸门开,又合
我乘着末班车驶向
地底深处的
未知尽头
导师评语:此诗以地铁车厢与校园的自然/人文景观为对比,探讨现代人被科技异化的麻木状态(车厢)与鲜活生命力(校园)的冲突,最终回归对未来的迷茫。尝试通过:空间转换(车厢、天桥、校园)建构叙事层次意象对立;(科技/自然、僵/生机)强化主题张力时间隐喻;(猫尾、年轮、四年刮痕)表达青春易逝。唯「四年刮痕/铬在玻璃表面」中「铬」(金属)与时间痕迹的关联不够自然。
围——新界西生活记 ●邝玉龄 中文系三年级
初来香港时,我住在天水围。
那时只觉得这城市像一只巨大的铁笼子,将人密密实实地关在里面。屋苑楼与楼之间挨得极近,从我家窗口伸出手去,几乎能碰到对面人家的晾衣杆。
母亲总说我们幸运,住的是私人屋苑,比公屋宽敞些。但所谓「宽敞」,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
四口人挤在三十多平米的空间里,转身都要预先打招呼。弟弟的玩具和我的书本常年争夺着沙发底下那点可怜的储物空间,胜负难分。
天水围的街道像是被人用力捏过的纸条,皱巴巴地蜷曲着。行人道上永远挤满了人,大家摩肩接踵地走着,却都默契地保持着一种奇异的沉默。
初来时我很不习惯,总觉得这么多人却如此安静,实在诡异。后来才明白,在这方寸之地,沉默是最体面的相处之道。
上屋苑会所的设施清单看起来很长:游泳池、健身房、阅读室……
实际每个都小得可怜。游泳池像个大浴缸,挤满了学游泳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健身房里三台跑步机永远有人在用;所谓的阅读室不过是个摆放了十几本书的玻璃柜子。
周末时,我和弟弟常常在屋苑里转上好几圈,最后只能坐在大堂的长椅上发呆。
母亲说我们在内地时抱怨城市太大,去哪都要坐车,现在又嫌地方太小无处可去,真是难伺候。
就这样过了七年。七年里,我和弟弟都长高了,家里的东西也像会繁殖似的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父亲看着弟弟的自行车,卡在门口进不来的样子,叹了口气说:「搬吧。」
我们搬到了元朗的村屋。虽然离天水围不过几站轻铁的距离,却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村屋没有会所,没有管理员,开门就是街道。第一次站在三层小楼里时,我竟有些不适应——原来伸直手臂真的可以碰不到墙的。
其实在天水围住时,我们就常来元朗。每个周六,我都要去喜利大厦上钢琴课。
最初,觉得元朗像个迷宫,那些横七竖八的小巷仿佛会自己变换位置。大马路旁突然岔出的小路,走着走着又分出几条更小的岔道。
我常常在找路时误入一些奇怪的地方:藏着老式茶餐厅的后巷,堆满五金杂货的骑楼底,甚至是某户人家的后院。
有次为了找近路,我钻进一条小巷,结果绕了半小时才回到大路上,钢琴课早已开始。奇怪的是,这种迷路的经历并不让人烦躁。
在天水围,迷路是不可能的——每条路都笔直地通向某个明确的目的地。而在元朗,迷路反而成了探索的乐趣。
大约两三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导航了。那些曾经看似相同的街道,在我脑中已经自动绘制成了一张立体地图。
但真正了解元朗,还是搬来之后的事。村屋的生活让我有了更多闲逛的理由和机会。不用再像从前那样,每次来元朗都匆匆赶去某个特定地点,然后又匆匆返回天水围的「围城」里。
我开始注意到元朗的肌理:以青山公路为中轴,向两侧延伸出无数毛细血管般的小街巷。轻铁像一条银色的丝带,将这些脉络串联起来。
元朗的丰富是慢慢显现的。朋友第一次来我家玩时,惊讶地说:「你们元朗怎么什么都有?」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不知不觉中,这里已经能满足生活的所有需求。
想吃地道的?街市旁的老字号粥粉面店开了三十年;想喝奶茶?方圆百米内能数出五家不同品牌的店;就连宠物都有专门的街区,从粮食到美容一应俱全。
最妙的是,这些店铺并非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商场里,而是随意地散落在街巷各处。转角可能遇见的不是爱,而是一家开了四十年的凉茶铺。老板不用问就知道你要喝什么——元朗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凉茶偏好,我家楼下那家记得我父亲总要「廿四味加甜」,母亲爱「雪梨茶走冰」。
轻铁是元朗的脉搏。住在天水围时,我觉得轻铁只是交通工具;现在才明白它是元朗人的生活时钟。
清晨赶着上班的人潮,下午主妇们买菜时的悠闲步伐,晚上补习学生匆忙的脚步,都在轻铁站里交汇。我常想,若是把元朗的轻铁路线图叠放在旧时的水系图上,大概能重合个七八分——人们依然沿着水的轨迹生活,只是铁轨代替了河流。
五年过去,我已经能像本地人一样,在街市里挑最新鲜的菜,知道哪家茶餐厅的菠萝油最好吃,甚至能说出几条只有老元朗才知道的捷径。
带朋友逛元朗时,我像个炫耀自家后院的孩童,一定要带他们去吃我认为最好吃的鸡蛋仔,走我认为最有味道的老街。
朋友常说元朗人幸福,我想他们说得不错。这种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一切都恰到好处地存在着——不至于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也不会少到令人捉襟见肘。
就像我家村屋的天台,不大不小,刚好够摆四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傍晚时分,我们一家常坐在那里,看着轻铁从远处驶过,车灯在暮色中划出一道流动的光痕。
从天水围到元朗,不过是从一个「围」到了另一个「围」。但这两个「围」字,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困住人的围城,一个是围起来的家园。
导师评语:此文透过对比天水围与元朗的居住体验,探讨「围」的两种意义「围城」与「家园」。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展现香港新界西的市井生活,既有对空间压迫的批判(天水围),也有对社区温情的赞美(元朗),最终落脚于「家」的归属感。主题兼具社会性与个人性。中间过渡稍显突兀(如「就这样过了七年」后可加入承接);元朗部分的「迷路」段落可更紧密衔接后文的「探索乐」。

牛牛幻想曲 ●莫嘉瑶 中文系三年级
我听见。哞——
天然的闹钟响起。我套上制服时,邻居张师奶牵着她的霍尔斯坦牛路过窗下,牛铃叮当混着她尖锐又急速的嗓门:「落街饮早茶要趁早等阵天水围班塞牛大军杀到屯门公路又要打蛇饼!」
哒。哒。哒。
眼前的景色是这样的:戴金丝眼镜的银行经理骑着娟珊牛,西装口袋插着《星岛日报》,牛角挂着Starbucks外带杯,全身上下无一不精致。穿紧身运动裤的师奶驾驭印度瘤牛,牛背上绑着刚出炉的菠萝包,面粉香与牛粪味在轻铁站前交缠。最威风的还得是地产经纪,他们跨坐通体雪白的牦牛,牛蹄包满金边,蹄铁敲击青砖路面的节奏,令人血脉贲张。
以上……
只是我的想像罢了。
我曾坚信遥远的西新界人血液里流淌着牧草汁液。中三那年在地理课本空白处涂鸦,将轻铁路线图改画成牛种分布图。我想,610线是霍尔斯坦牛,温吞但准时;507线是印度瘤牛,脾气暴躁却脚程快;506P线嘛则是杂牌老黄牛,年老又不能缺少的存在。
直到那一年——
我来到了,屯门。
那天我站在屯门市广场天桥上数了整整三小时,穿梭而过的只有九千六百七十二辆汽车与四十三架单车。还有,零只牛。
原来,关于牛的记忆,终究是都市传说嫁接的枝桠。
然后,我坐上了轻铁,507。轻铁慢慢行驶,驶过V city。我又想起了那个曾经反覆出现的画面。一个男孩骑着牛从屯门轻铁站穿越V city,最后在一田橱窗前表演急停,还记得避开拖着粉红行李箱的水货客。
精彩。
为此,我还特意制作了一份《屯门牛路守则》。 《屯门牛路守则》第三十七条:
「牛只进入V city须佩戴防撞角套,以免刮花名店橱窗倒影」。
以上……
不过是我的想像罢了。
车厢里飘浮着不同语言的交谈声,韩妆少女与跨境学童共享着摇晃的扶手杆。
我将额头贴上玻璃窗,看那些曾幻想牛只奔驰的街道——
经过蔡意桥。不知谁家阳台飘来蒸咸鱼的香气,混着巴士的柴油味,在屯门河面织成半咸淡的雾。轻铁的影子随着脑海中的幻想越拉越长,越来越长,渐渐盖过整个屯门,最后消融在晨雾之中。
某天下班我去屯门兆麟政府综合大楼办理护照,在轻铁站邂逅牵牛只散步的老伯,牛只颈上系着铜铃。 「唉,几时先可以储够钱,将呢只老牛换架车。」话毕,只见身旁的一只牛突然撅起后蹄,将阿伯的渔夫帽踢进屯门河。
以上……
可能又是我的想像?
那只是一只调皮的大狗踢翻主人的帽子——那顶浮沉的帽子像一片牛粪,顺着水流漂向对岸正在施工的新楼宇?
《屯门牛路守则》第五条:「牛只造成异物入河事故,须缴交牛蹄清洁费,并暂停该牛只上路资格一年。」《屯门牛路守则》第六条:「牛只不得不……」又扯远了。
以上……
又再是我的想像罢了?
晚饭过后,我总是喜欢在屯门游荡。从兆康走到新墟,从蓝地走到麒麟,从屯门码头走到蝴蝶湾。而往往这时候,总会看见骑行单车者们蜿蜒如缎带,闪着车头灯组成一道流动的彩虹。
我忽然羡慕起那些踩单车的人。
在九龙区长大的我很少接触单车,甚至想在市区中心寻觅单车的踪影,也不见一辆。说来惭愧,我竟不会踩单车。他们在轻铁站旁的金属架前弯腰解锁,动作娴熟如西部牛仔系缰绳。
这,或许才是屯门真正的「牛」。
当市区人为找不到泊车位苦恼时,这里的屋村总能从角落变出缠着胶带的单车架,生锈的钢管上开出岁月的铁锈花。
每天坐上62X巴士来往屯门与九龙,看着阳光在车厢地板上切割出明暗方格。
此刻,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身穿正装的女士正用手机拍摄沿途街景,河畔开满紫荆的单车径,天桥下玩滑板的少年,商场外墙轮播的电子广告。当车辆转入隧道时,玻璃窗突然变成镜面,映出我们这群沙丁鱼乘客的疲惫面孔——那些幻想骑牛上学上班的执念,或许只是对边陲地带的一种迂回想像。
我终究没见过传说中的「塞牛大军」。
下车后,看见穿瑜伽裤的母亲拎着Donki环保袋走来,她身后正是举办美食节的屯门市广场。我们穿过停满单车的屯门公园,不锈钢车架在夕照下燃成一片金属草原。暮色中有人骑着单车掠过,车轮辗碎我投在地上的影子。突然我清楚看见生锈踏板旋转成青铜牛铃。那一瞬仿佛瞥见骑牛少年在公路上慢悠悠地晃悠,我眼巴巴地仔细盯着那牛背上晃来晃去的身影,而牛蹄扬起尘土,夕阳正将背后的轻铁轨道镀成金黄的缰绳。此时河面漂来的塑胶帽忽然立起尖角,而母亲购物袋渗出的血水正灌溉着水泥缝隙。我终于听懂——那彻夜不休的「哞」声,原是整个城市在反刍自己的铁胃。
导师评语:此文透过「牛」的虚实交错,隐喻都市化对地方文化的消解,主题新颖且富诗意。但「单车替代牛」的转折稍显突兀,可加强连结(如单车铃声与牛铃的呼应),中段《屯门牛路守则》重复略显冗赘,可精简条目或融入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