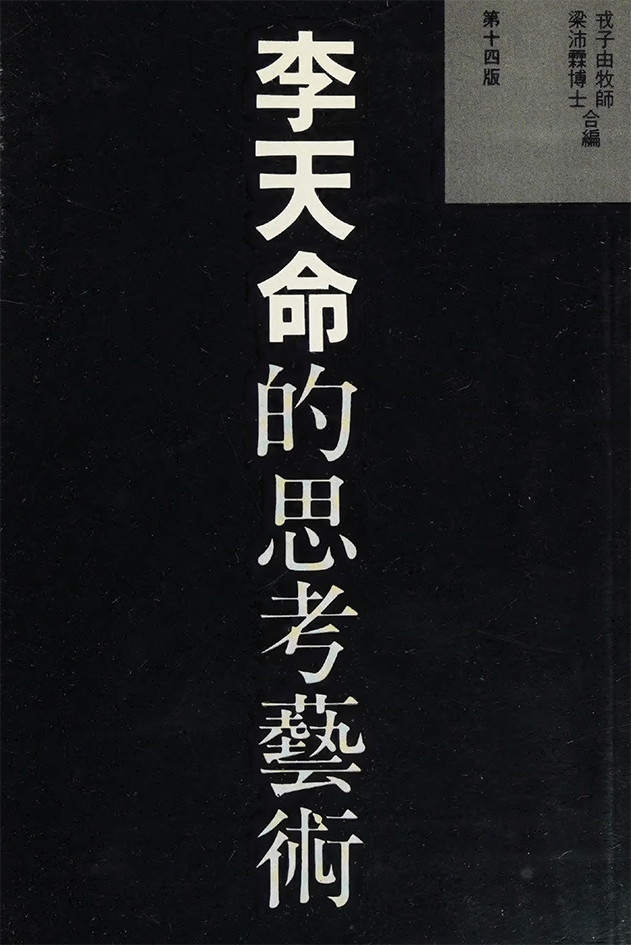走笔至此,才惊觉校友会已踏入耳顺之年──不管怎样,她是一条坚韧的感情链条,牵引着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和我那难以磨灭的回忆。
印记中的母校,原是坐落在香港西环青莲台上。每当拾级而登上青莲台百多级的石阶,便会泛起很多感触。脚下的石阶依然那么实在、默默、无怨、无悔,而作为与母校阔别逾六十载的我,却要穿过这漫长的时光隧道,去捕捉学龄期的一鳞片爪。
六十年前,在中学求学时期,我是属于内向的人,除了念书、阅读,剩下的时间便去组织文社、编辑文稿、刻蜡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香港文社潮奠定了香港本土文学。作为临毕业的中五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个豪志文社。文社名是取其豪情壮志之意,这是当年一班年轻小伙子的心态。套当时流行话是「热火朝天」,真有点豪气干云之概,大家都很想干一番文学事业。
文社的成员大部分是同班的同学,也有个别读他校的中学生。我们有定期聚会,谈文论艺,并把社员的文稿汇编成《豪志文摘》,每月出一期。当年影印机和电脑照晒植字,还没有出世,文稿全部靠一双手一横一撇刻在蜡板上,然后一张张油印出来,操作全是手工式的。
我们基本利用别人在看电视、玩耍的时间去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的。由于文社都有共同的爱好、兴趣,正如梁启超指出:「文学是人生最高的嗜好」,在这崇高意念的感召下,我们利用课余的有限时间去编写一本文学杂志,很多时候是很疲累和吃力的,但我们大家协作得很好,不以为苦,从无怨言。
在我们弄文社、编油印文学刊物的时候,一直得到黄秀雅国文老师的从旁支持、鼓励。当时正值文革,文艺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其间我们的文社也被勒令解散,当我们感到彷徨、困惑的时候,黄老师也一直安慰、开解我们。
黄老师已作古多年。我在她去世前探望过她一趟,是一次颇伤感的见面。她住在西贡一间村屋。
那天我先去探望在香港城市大学当兼职教授的刘再复兄。再复兄的大千金刘剑梅刚从美国来看望双亲。她是才女,文章写得好,年纪轻轻便担任华盛顿马里兰大学永久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她听说我去探访中学老师,表示愿意陪我走一趟。
甫出门,老天涮地便变了脸,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们几经波折,终于找到黄老师的寓所,门前的一泓积水,已没及足踝。我们只好脱了鞋,赤足淌水过去。
开门的是黄老师的千金梁焕仪,她是我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入到门内,孱羸的黄老师直挺挺地坐在客厅的梳发上,我们向她打招呼,她完全没有反应,目光有点涣散,只有嘴角仍挂着一丝笑容。焕仪说黄老师患了阿兹海默症。
我们相对无言,只闻窗外的雨声恍如银河倒泻,越下越大,电光石火,加上霹雳的行雷声,场景令人有点震撼。我们稍坐片刻便告别了。
雨还在肆虐着,剑梅说:「这场面太沉重了!」我说:「这个时代,我们都活得沉重。」这一次探访,竟成了与黄老师最后的诀别。
三十年后的一天,市政局的留驻作家吴萱人兄来访问,要我谈一谈当年豪志文社的情况,并准备编入他们的研究项目──香港文社的集子内。这对三十年前的辛勤耕耘的文社成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回馈。
毕业后,当年参加文社的同学星散了,不少人已从事别的行当,而我仍在文学道路上蹒跚地匍匐着,不改初衷。如果在我初期创作道路上没有黄老师的谆谆策励,也许举步要更来得维艰些。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黄老师早已远去了。她的音容宛在,她诲人不倦的精神与及那一次雷雨中沉重的会见,仿佛在昨天。现实是,昨天已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九位豪志文社的成员,其中已有二位先后下世了,剩下我们的七位,也偶尔聚会,都已呈老态,但心中仿佛还有点文学薪火的余烬。
走笔至此,才惊觉校友会已踏入耳顺之年──不管怎样,她是一条坚韧的感情链条,牵引着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和我那难以磨灭的回忆。
(作者为香港散文作家。)
【乡港情】■ 楼上书店 ●文、图 绿骑士
像石丛中生长的花儿,香港二楼书店是一种边缘的奇异生态。在最挤闹的地方散发缕缕书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人风景。
楼上书店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都是由追寻理想的知识分子经营,许多老板是卧虎藏龙。七十年代,以各种渠道收集到中国内地因文革被批斗的作家作品,又常引进台湾作家作品,成为知识交汇的宝藏洞。八九十年代更蓬勃,对中华文化承传贡献极大,更灌溉滋润了不少文艺青年成长。但二○○三年沙士重创,加上其他原因,纷纷结业,如洪叶、青文、紫罗兰,曙光等,使人无限惋惜。
这行业小众、冷门、毛利低,更要对付昂贵租金。在商业巨潮中,那些爱书痴人固执地创造一个丰富的小天地,浪漫到骨子里。尤其怀念可爱的见山书店。这些独立书店相继倒下,但又有勇敢的新来者。
有些同时结合咖啡店、举办艺文或社区活动,空间洋溢着亲切氛围,成为一种生活姿态。现在仍然活跃的楼上书店如老牌的乐文书店、田园书屋、「猫书店」森记图书等,较后起的有的充满个性的艺鹄、一拳、界限、长梦等等,不能尽录。接近百老汇电影中心的「Kubrick」文化空间和佐敦突破书廊均非二楼书店,都各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有些书店设在工厂区、新界、离岛。如在大埔有解忧旧书店、长洲有渡日书店,部分更兼售粮油杂货,满满人间烟火气;锦田比比书屋田园气息最吸引人,坪洲南湾书店亲近岛民。西贡的神话书店,试业五年后在今年十一月一日正式营业,店主说:「神话故事一定未完。」楼上书店像神话,也一定未完。
(作者为旅法香港作家、画家。)

【评论】■ 都市游牧者的香港稜鏡 ●邓倩倩
程皎旸新作《打风》的装帧深谙搭配,左上方是半边白色封套,好似半遮面的面纱,取下来方见本书全貌:护封是一片湛蓝的海域,如同微皱的锡纸,泛着银白的碎光,上面停泊着大小不一的船只,弥散着咸腥的海水味与冲鼻的柴油味;封面是雨幕中的香港街景,几辆双层巴士被晕染成柔和的水彩画。
这种装帧的设计揭示出都市的游牧密码:先拥有一个临时的外壳,才是触及香港肌理的先决条件。 《打风》囊括了十一篇小说,犹如十一面多稜鏡,从多个角度折射南方城市中女性生存图景:语言隔膜、社交壁垒与身份悬置。但作者程皎旸并没有止步于文化冲突的痛苦中,而是凝望着她们在都市沥青道路上的足迹,让这些在临时坐标上的生存印记成为永恒。
在迁徙的伊始,缺少归属感的不适必然带来边缘的体验,这些体验无不跃然于文本上。 〈条形码迷宫〉中的阿Mint初到香港,在陌生的语言星系里,拖着巨大的行李箱,不知所措,被嘈杂而急迫的人群推搡到边缘。 〈香港快车〉里的海莉对一表人才的Jari一见倾心,幻想与他有惊为天人的感情线,结果他的亲近无非是为了写论文,并划清彼此的界限——「我不是不想带妳去party,但我们是不同的social group。」在语言混搭的交际网里,英伦英语、粤语口语与商业行话构成多声部的空间,但造成交流困难的实质上是地位与身份。

城市中的当代游牧者
这种疏离感很快被另一种更普遍的都市心情所覆盖。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新式牧场,充斥着金钱狂欢的气息,游牧者面临着荒诞的异化。 〈金丝虫〉以吸心的血和吃心的肉的金丝虫作为全篇的核心意象,直接点明这个时代的症候,「城市俨然已成了一座座巨大的商城,所有的一切都在被贩卖,贩卖衣食住行,贩卖文化,贩卖梦想,贩卖教育,贩卖未来。也许有一天,大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手上生出了条形码。人们既创造商品,也成了商品……」这一番直言袒露,瞬间暴露了当代游牧者无法逃离的宿命,在消费者与商品两者之间不断切换角色。
面对这种情形,游牧者思考出一种独特的应对方式,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搭建可拆卸的帐篷,程皎旸便将这种栖息智慧运用到现实里,她允许超自然的力量介入文字里,让故事游离于虚无与真实之间,打乱了人们固有的认知秩序。 〈纸皮龟宅〉里的驼背老人以拾荒为业,长期作为城市光鲜表象背后的暗物质,因为他们靠着纸皮砌成驼背,又把驼背撕扯成龟壳,让自己的肉身有了容身之处,迅速引起了房地产公司的兴趣。这些公司顺势推出了「陆龟侠主题」的租赁服务,让老龄人口艰难谋生的处境化为操纵楼市的手段。这个令人战栗的讽刺手法,如同一个X光机,照见事件本质:空间分配绝不只是物理原因,而是权力蔓延的显影液。
爱情在这种流动的社会形态里也难逃毒手,古典式的守护关系早已失落,快餐与娱乐至上的情感成了人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海胆刺孩〉里洗头妹「我」在阿妈去世后,开始了快活的人生,即在社交软件tinder上认识来自五花八门的男人,并笃定只有初识的男人才会对自己好。 〈狗人〉的情感观更是赤裸的残忍,卡尼卡不满苏叶找狗人惩罚骚扰自己的戴文,并展开一系列的责问,「妳以为我是傻子吗?让戴文摸一下,就可以多拿到一个项目,为什么妳要多管闲事?」亲密关系沦为生存策略,它们具备帐篷随建随拆的便利,却兼顾不了毡房的温暖。在冷静展示的背后,程皎旸的笔端如夜风掠过帐篷的绳索,仿佛是作者的一声叹息。
此外,程皎旸还准备了一个颇神秘的彩蛋,香港只是尚未写完的迁徙日志,里面还夹杂着一张全球的游牧地图。如果说〈金丝虫〉是香港商品化带来的反讽寓言,那么〈逃出棕榈寨〉便将这一困境拓展到异域资本的狩猎场。 「我」来棕榈寨追寻母亲作为情色演员的往事,从憎恨她给我下的贫民窟的魔咒到谅解她用身体换取生存筹码,一切的罪孽都逃不过资本设定的游牧法则。
十四年的在港岁月使得程皎旸成为都市游牧者的口述代言人,她陆续推出了《乌鸦在港岛线起飞》、《飞往无重岛》以及《打风》这三部以香港为书写背景的小说集,致敬着自己的维港世界。 《打风》取自粤语中的「台风」意,里面的十一位女性也时刻处于台风即将来袭的临界点——签证、租约、感情即将画上句号。由此,这本书勾勒出都市游牧群像独特的生存方式,即便不堪重负,但血性难凉。程皎旸笔耕不辍地证明,最港味的小说,往往被游走于岛内与岛外的人所执笔。
(作者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课程,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诗两首 ●张志豪
看 雨
风和三月复还寒,不住重云树不安。
忽堕雷霆山石雨,人惊人窜我闲看。
《明报月刊》创刊六十周年庆
明月墨香盈甲子,光华灿烂汇群星。
无端世态纷纭事,一盏伴刊读不停。
(作者为本版执行编辑、香港作家联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