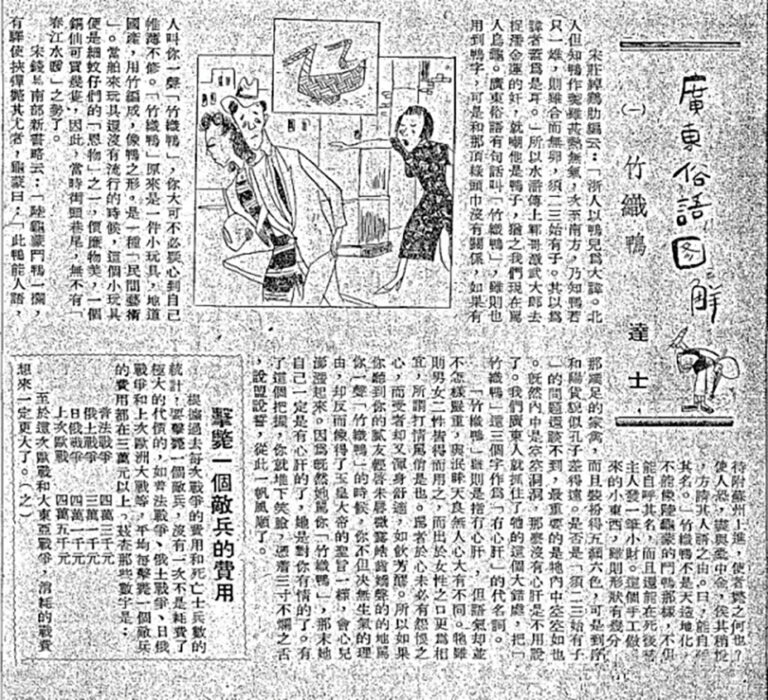编按:《香港文学》四十年来炼就了一条触及四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链」,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贡献重大。二○二五年一月五至十日,「四十芳华——《香港文学》四十周年志庆书画展暨作家手迹展」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本文记述了开幕式、展览现场及《我与〈香港文学〉》新书首发仪式的盛况。

艺文双举群英荟萃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为期六日的「四十芳华—《香港文学》四十周年志庆书画展暨作家手迹展」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步入展览厅,一片红映入眼帘,像匹红绸挂在门楣—那是此次展览的前言板。前言板上过往期刊精选封面拼成「40」字样,衬着背景的正红,如滚滚红尘中的海上花,铺展成一条花路,连结维港两岸—不止是维港,更连结世界。 《香港文学》四十年来一直秉持自创刊以来的办刊宗旨,「立足本土,兼顾海内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在扎根香港的同时,为全世界华文作者提供了一个高品位的纯文学平台,在刘以鬯、陶然、周洁茹、游江四任总编辑的耕耘下,搭建起连结世界华文文学的桥梁,成就斐然。前言板上四个金色书法字「四十芳华」非常显眼,是由书法名家秦岭雪所写,笔走龙蛇,一笔写下《香港文学》走过的四十年的金色的来路。读过标题,再细看前言的一个个蝇头小字,《香港文学》总编辑游江介绍了本次书画展暨作家手迹展的概况,共展出来自香港、北京、广州、深圳、济南、西安、福州、纽约、巴黎等世界各地的书画作品八十多幅,及香港文学出版社珍藏作家手稿、书信等六十余件。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展览的大部分作者既是书画家,又是作家、学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集诗、书、画于一身的学养。
漫步展厅,四面墙上挂着的字画,如同开了一扇扇窗,透过窗能够望见园林里的花树—遒劲的书法是虬枝,传神的国画是繁花。虽然身在室内,但已经望见窗外的春——《香港文学》走过的四十年春。展览厅三边摆着玻璃展柜,陈放刘以鬯、也斯、王鼎钧等作家的手稿、手迹、书信,有的纸张已经泛黄,岁月的印记铺满其上,但纸短情长,脆薄的纸张承载着的文思不随岁月褪色,反而历久弥新。无论是精美的画作,还是珍贵的手迹,都在诉说着创作者的心声和对文学艺术的热爱,现场参观者也被深深地感染,不时驻足看得神往,文学与艺术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时空,触动心灵。
临近开幕,展览厅内人头攒动,受邀嘉宾们在前台签到后,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星光熠熠,是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一次盛会,空中仿佛都是思想与思想擦出的火花。

四十不惑再续芳华
开幕式于下午五时正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祝贺《香港文学》创刊四十周年,肯定了《香港文学》为推动香港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表示:「特区政府在去年十一月公布了《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为香港未来的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发展订下清晰愿景、原则和发展方向。未来,特区政府会与不同业界持份者和本地文艺社群共同合作,携手推动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特首的一番祝贺极大地振奋了现场观众,令文艺界人士备受鼓舞。

随后,香港文学出版社社长李国红代表主办方致辞,向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香港文学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并向各位嘉宾莅临今天活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谢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陈咏雯对《香港文学》创刊四十周年表达祝贺,并祝愿本次展览圆满举行。她表示,《香港文学》四十年来坚持不懈,在香港文化事业发展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近期和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小说写作坊」就是积极推广文化创作、艺术欣赏的好例子。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杂志社长兼总编辑王世孝致辞祝贺,分享和香港文学的文学缘,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加强沟通合作。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白杨致辞祝贺,她说:「《香港文学》关注港澳台地区及海内外华人作家的创作动态,以开放性和独特性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多样性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注入了活力与动能,成为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

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致辞祝贺,他表示文学与艺术不分家,文学家也是艺术家,好的画作也蕴含文学色彩。

文墨飘香情意浓浓
开幕式的高潮是剪彩仪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陈咏雯、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文部副部长李曙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港岛工作部副部长杨成伟、外交部驻港公署国际部主任王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马逢国、香港中央图书馆总馆长李美玲、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世孝、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白杨、刘以鬯太太罗佩云、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吴君、华丰国货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新、香港文学馆署理馆长罗光萍、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郑培凯与香港文学出版社社长李国红、香港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游江共同为开幕式剪彩。随着主持人宣布剪彩仪式即将开始,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每位嘉宾手持一把金色剪刀,象征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当主持人倒数「三、二、一」时,全场气氛达到高潮,嘉宾们同步剪下了象征四十周年志庆的彩带。彩带一剪而落,现场掌声雷动,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我与〈香港文学〉》新书首发仪式随后举行,新书精选「我与《香港文学》」征文活动佳作六十余篇,讲述作者、学者、读者与《香港文学》的文字缘份,中国书协香港分会副主席秦岭雪致辞。该书作家代表秦岭雪、周蜜蜜、梅子、黄维梁、邵栋、程皎旸与该书主编游江共同为高达两米的新书模型揭幕。当盖住模型的红绸布缓缓滑落,如岁月之河缓缓而下,现场嘉宾沉浸其中,无不感受到时间的力量、文字的力量。
在《香港文学》这个平台上,无数来自香港本土、内地及海外的作家留下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名家云集,佳作纷呈,其中不少首发的作品都是文学名篇。李国红、游江为捐赠书画作品及手稿的作家、艺术家颁发收藏证书,并再次感谢与《香港文学》一路携手前行并给予支持的各界朋友,尤其是作家、学者与广大读者朋友。
活动虽接近尾声,但嘉宾们的热情有增无减,纷纷表示对《香港文学》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四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成长与成熟;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则意味着历史与传承。 《香港文学》用四十年的时间,炼就了一条触及四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链」,连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读者、研究者,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希望这条文学链能随岁月之河一直绵延、铺展,抵达下一个四十年、一百年。
(本文图片由香港文学出版社提供。作者为《香港文学》编辑。)
【评论】■
所有啡树叶都不会过期:第七次观《重庆森林》后散记
●曾繁裕
按健力士纪录,一位影迷曾看了《蜘蛛侠:不战无归》(二○二一)二百九十二次,期间没使用手机、瞌睡和大小便,不知他是否只为刷纪录?看最后一次的感觉如何?往后会否继续看继续破纪录?能否把电影的所有台词和情节倒背如流?
与他相比,只看七次《重庆森林》(一九九四)当然不值一提,但,当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跟电影擦身而过,且对它们一无所知,重看,始终有其意义。
二○二四年四月三十日晚上七时四十分,重庆大厦对面的iSQUARE内,英皇戏院上映了《重庆森林(4K修复版)》,纪念何志武(金城武饰)在三十年前的夜里,买到最后一罐凤梨罐头。修复,是经典重现的噱头,梁朝伟的另一代表作《悲情城市》(一九八九)也借「4K」之名,得以在前年于多间香港戏院公映。无可厚非的是,戏院需要票房支持,但想深一层,经典作为历史精华,必有其经济价值,若观众只能在电影节和百老汇电影中心重温,实在非常可惜。在淡市之时,让选播经典在各大院线流行起来,使消费经典成为大众日常,定不会扼杀创作,反而有利本地电影产业长远的供求发展。
浓重的诗意金句精彩的情节设计
回说电影本身,小时候不认识王家卫、看不懂《重庆森林》(一九九四),不理解两条切断的故事线有何关连,也不理解随机的诗性就存在于无关与有关之间,只是看罢脑里不断回荡着:「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ey……」那时英文差,不明所以,网络不发达,大了才找回原曲,知道歌中的加州梦与女主角失约相关。也许王家卫电影的吸引力就在于创制一种与回忆共生、即使模糊也难磨灭的节律,隐约诱发情感牵连,久久不散而引人细究。
大学修读一门中西电影课,陆续观赏王家卫的全部电影,尤爱《阿飞正传》(一九九○),也看了六七次,总觉观影时光飞快,台词往往耐嚼:「我听人讲,呢个世界上有一种雀仔系冇脚慨……」、「每个人都会经过呢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系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连星爷也常以戏谑方式仿效,如《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 :「曾经有一份至真慨爱情摆喺我面前……如果系都要喺呢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当中,「一万年」正正呼应何志武的「 Call机」密码「爱你一万年」。
王家卫大概是早期最有意识地量产金句与潮文的导演,方向围绕记忆、聚散、情恨、时间之类,像昆德拉,但比他更纯粹、诗意更浓重,新近的香港电影金句常单薄地食字、卖弄情怀、做大总结,境界相距甚远。
《重庆森林》之精彩,也在于情节设计:彻夜进食来为感情悼亡、失恋者把家中所有死物拟人并与之对话、用前女友留下的锁匙偷进意中人家并替他打扫……既写实又象征,场景浅近但经验独特,深进人内心的渴望。虽然看第七次时,许多情节与台词未出现已可预期,但即使掌握,也不觉媚俗,且能被丰富的小幽默触动,如听到阿菲(王菲饰)被六六三(梁朝伟饰)发现置身他家时,说:「又系你叫人得闲嚟坐下慨!」不禁失笑。
班底和题材成就经典
可一不可再,总觉王家卫较后的作品《2046》(二○○四)、《我的蓝莓之夜》(二○○七)、《一代宗师》(二○一三),以至电视剧《繁花》(二○二三至二○二四),都难再保持「耐力」,大抵与班底和题材相关。一则班底无常,不能每套电影用同一班演员、同一班制作人员,发挥相同的化学作用,比如《2046》中的章子怡,总觉不合王家卫的诗味;二则无论如何上乘的素材,都不能无限循环再造,要不尽用,要不留余,让价值延续。无疑,王家卫唯美之力很深,每造一部电影,都像造一枚防伪标签,以至自我复制也显然。从主观经验看来,《阿飞正传》与《花样年华》(二○○○)已用尽王家卫的旧香港资源,以致《2046》需走科幻植入之途,而《繁花》因篇幅浩长,常重复过往电影的造句、造情、造局之法,让熟悉紧凑版王氏出品的观众难觉痛快。
说到最后,不禁惋惜,《繁花》虽然吹捧者众,但看完便罢,还不如重温《重庆森林》般泛动心绪。似乎过期与否,不在于拍摄的时代、题材涉及的时代、导演的经验值等,而在于如浪漫般难解的机缘,于此,或许可反思何志武的一段话及话后如何:「新鲜新鲜,咩嘢新鲜啊?就系你呢种人啊,贪新忘旧慨!喂,你知唔知整罐菠萝嘥几多心机啊吓?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话唔要就唔要啊?你有无谂过罐头慨感受啊?」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