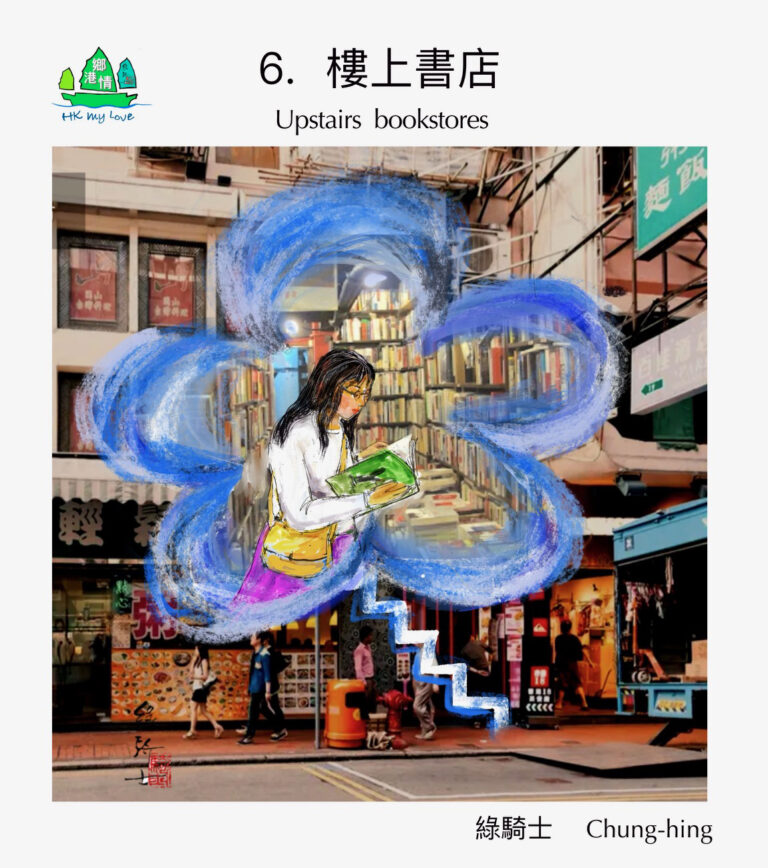编按:「这些年,这里的天更蓝了,水更绿了,越来越多的鹭鸟飞来天蓝、水清、岸绿的星湖繁衍生息。」肇庆老城中的山水景致吸引各种鸟类。 「『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这句话讲的不正是眼前的这个小鸟的新天堂吗?」
长时间伏案工作,有时候偶然抬头,看窗外的湖光山色,蓝天白云,成群结队自由飞过的鹭鸟,会有种穿越时空看年轻时自己的感觉,尽管随心所欲早已渐行渐远,但还是觉得时光未老,尚能继续前行。
在倍感疲惫的时候,这座山环水抱的城市,这座因端砚而闻名古称端州的城市,这座山好水好湖好、砚端政端人端的城市,这座因宋徽宗认为会给他带来喜庆而被命名为肇庆的古老城市,总会给你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每周的一两个下午下班时,会选择沿着星湖边那条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的堤路,慢慢的走回家。
肇庆的天更蓝了,水更绿了。天空似乎触手可及,水光潋灧中,远山近树全倒影在湖中,清晰可见。 「水似万尺锦缎接远天,岩如七星飞降落山前……」在浮动的光影和习习凉风中,一边踽踽独行,一边轻声哼着这首轻快的广东第一首粤语流行曲,案牍之劳形瞬间烟消云散。
湖中,状如北斗七星排列的七座岩峰倒影于湖中与天光云影融为一体,会让走在湖边的人有种徜徉天际的感觉,这不就是水天一色吗?这不就是水清树绿景美人悦吗?湖上,七座岩峰陡如峭壁,壁上岩缝日积月累竟积攒出肥沃的土壤,长出了许多姿态各异生命力顽强的剑花与鸡蛋花树,形成蔚为壮观的「峭壁森林」。湖下,湖水清澈见底,长满随波飘摇的长长水草,又俨然另外一片「水下森林」。竹筏划过水面,惊起几只小水鸭,振翅而起。面对如此美景,少年时一个猛子扎进老家小河穿越摇曳水草追逐鱼群与蝌蚪群的画面蓦地重现。天光水色之间,仿佛每一条飘动的水草,都是蔓延的童年记忆。
夕阳西下,远处慢慢有无数的鹭鸟成群结队飞过来。它们时而低飞盘旋,时而在湖面觅食,时而在枝头嬉戏。湖上几个小岛的茂密树林上,全站满了大大小小的鸟。
「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看清楚这只,又看漏了那只,看见了那只,第三只又飞走了。」这不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巴金笔下的「小鸟天堂」吗?
蓦然惊觉,这些年,这里的天更蓝了,水更绿了,越来越多的鹭鸟飞来天蓝、水清、岸绿的星湖繁衍生息。不经意之间,竟慢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鹭鸟纷飞」、「万鸟投林」的美景。忽然间觉得,「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这句话讲的不正是眼前的这个小鸟的新天堂吗?
这一刻,不由想起生斯长于斯的古端州人,其实很早就有环保的意识。四百多年前的明万历年间,两广总督戴耀为保护七星岩不受破坏,便于湖对岸的石室岩洞外东壁刻下「泽梁无禁,岩石勿伐」八个石刻大字,意思是说这里捕鱼不加禁止,砍伐树木,破坏山岩,决不允许。
「肇庆是一个能真正连接传统和现实的地方……」走下东堤时,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老师来肇庆看端砚时说过的那番话犹在耳畔:「每一方好的端砚,都能让人重识传统文化的精微和荣光。我常想起当年被贬岭南的苏东坡曾写信给黄庭坚说:『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每次来肇庆,我也会给远方的文友买一两方端砚。砚石里藏着那条珍贵的文化丝线,一直绵延至今……」
一只落单的归鸟张开翅膀,向湖中的小岛疾飞。天就快黑了,我加快脚步,朝家的方向走去。
我心安处是我家,愿每一只生活在这里的小鸟,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肇庆市作家协会主席。)

老城印记●黎晓阳
一眉弯月悄悄探出云影,像焦距捕捉到的影像,在朦胧的夜空中逐渐明亮、清晰,仿佛睡眼惺忪的美人舒开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
风,陶醉了。仿佛随月光款款而来,穿过幽邃的羚羊峡,掠过蜿蜒而秀丽的西江,像精灵一般闯进这座古老的端州城,敲响了宋城墙内永明宫上檐铃,铃声阵阵,犹如珠落银盘,惊飞了瓦脊上的一行飞鸟。
端州,又名端城,隶属广东肇庆市管辖,至今有两千多年历史。开国元勋叶剑英元帅就曾赋诗:「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盛赞肇庆星湖的秀美景色。
星湖,境如其名,星河之畔,湖光山色,如人间仙境。每至春季,十里湖堤,馥郁芬芳,七彩紫荆争相竞放。一朵朵,一簇簇,挂满枝头。倘若空中俯瞰,蜿蜒的湖岸线宛如一条七彩飞花的纽带,把山、湖、城、江,点缀得色彩斑斓。到了夏季,荷香瑟瑟,端州八景之一的「宝月台」荷花盛开。红荷翠叶,宛如城中镶嵌了一颗翡翠明珠。
我出生在端州的骑楼街,在那里长到七岁。那时老城很小,一条东西走向的骑楼街贯穿着老城区。骑楼街有书店、药房、面馆、打铁铺、杂货铺。除此以外,城内街巷纵横,四通八达,大大小小的胡同像人体复杂的脉络。如「米仓巷」、「担水巷」、「五经里」、「草鞋街」、「立新街」、「水师营」,九曲十八弯的胡同几乎每个名字背后都蕴含着一段历史或故事。当然,胡同虽老,却活像一个神采奕奕的老人,时刻充满着人间「烟火」。
那时候,水电资源仍十分紧缺。每到傍晚,常有穿着背心或光着膀子的人群在「骑楼」下歇息乘凉,妇女多是坐着小板凳围成一团,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借着路灯的光线做手上的活儿。更有什者,干脆把沙发搬到骑楼下南柯一梦……那年头,老街朝气蓬勃、乐也融融。 「青壮年」有永远忙不完的活,挑水、劈柴、买煤球,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小孩则是满街满巷地疯跑,到了开饭的时候,大人会站在屋前,吆喝几声,然后某个角落总会冒出个影子来,屁颠屁颠地往这边跑……
那时根本没有现代的娱乐设施,可骑楼老街却啥都是开心的玩意。哪怕是一根电杆、一条绳子、一个线圈、一个树杈,都可能想像出创意十足的游戏。总而言之,那时只有你想不到的,却没有做不到的。爬树攀竹,游泳翻墙,甚至打反叉倒立走路,几乎无所不能。
临近春节,老街年味就更浓了。端州人一直有包「裹蒸」的习俗。除夕前夕,家家户户在老街垒起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土灶,昼夜通明,熊熊的灶火遍布城中的街头巷尾,零落的鞭炮声已经告诉了你,新春将至。
八十年代初,我随父亲返回广州。临行前的一天,我坐上父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邻家谢姓女孩坐在车前架,我坐在车后架。那天她高兴得手舞足蹈,不时把手伸到后面拉我的手,我则躲在父亲身后扯她的衣角,她被逗得「格格」地笑。在往后很长的一段回忆里,父亲常常把她称做「格格」。或许,那天真无邪的笑声,从那一刻开始已经楔入父亲的记忆里。
那天,我第一次领略到被蓝天白云追逐的感觉,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来自陌生而艳羡的目光。两旁飞快倒退的房屋,路面像黏着轮子滚动起来,我们的情绪也跟随着轮子飞转起来。 「格格」将身子前倾,展开她柔弱的臂膀,那头平肩的秀发像被风吹散的青烟,在风中起舞。
啊,她宛如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对世界充满着无比的好奇和渴望。
望着那拉长而变形的影子,掠过斑驳的城垛,掠过深巷老宅中的院墙,忽然,我对省城那份热炽的向往消失了,心头莫名其妙地涌起一阵又一阵对老街的眷恋。
最终,我还是离开了这座城市。离别当天,「格格」站在送别的人群里,一言不发。她眼神流露出无奈与伤感。当我踏上客轮的那一刻,她终于飞奔过来,凑在我的耳边轻声说,骑楼前的砖缝里有一把钥匙,哪天我回来了,可以用它打开东厢的小书房。
离开老街我就再也没见过「格格」了。我曾在九十年代前回去过两趟,找到她楔入砖缝里的钥匙。那时「格格」一家搬离老街已经好几年了。记得推开那矮小的门扉,空气中充斥着一股陈旧的霉气,书架上挂着一把结他,书籍已经发黄了,被一块绣着「日月」的大红花布覆盖着。
离开「倒数」的人群,循着璀璨的灯光穿过人流如织的骑楼街,我在寻找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骑楼。忽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我发现东厢的门头上面写着「易灯书店」,我的脑海马上闪出了那块大红花布和结他……
(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驻村记》等。)
那年那月那座山●李罗斌
豆腐村的刘、黄两家同日娶亲,新郎官刘旺、黄柳是一块儿长大的哥们,好得不得了。
豆腐村以做豆腐出名,而尤以刘、黄两家做得最好,方圆百里闻名。村前有座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傍晚,当两支抬花轿迎亲的队伍在山里相遇时,山上突然下起了雨,两伙迎亲队伍放下花轿,躲进破庙里歇脚避雨。在雨中,只是苦了一对新娘,碍于礼数和面子,在大红花轿里动弹不得。幸好,只是阵雨,很快就停了,两伙人就又开始上路了。
混乱间,两伙人把花轿给调错了,刘旺的新娘抬进了黄柳的家,黄柳的新娘错入了刘旺的屋。本来,新郎官在揭新娘的红盖头时,就会发觉新娘弄错了,然后趁着夜色把新娘悄悄换过来,彼此都没损失,这个大笑话也就不会造成大错。可是,刘旺和黄柳都是贪杯之人,大喜之日,更是喝个酩酊大醉,入洞房时熄了灯火只顾抱着新娘亲热,大错便铸成了。
从此,两家成了世仇,互相不再来往。
二十年后的一个傍晚,还是那座山,打好两捆柴的黄柳儿子亮亮和外出卖豆腐的刘旺女儿晶晶遇上了,两人互不搭理,只顾赶路。这时,天突然瞬间漆黑了,飞沙走石,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落汤鸡似的亮亮和晶晶忙跑进破庙里,狂风暴雨的夜里是不能赶路回去的,不但可能遭到猛兽的攻击,而且还有坠落悬崖的危险。
亮亮很快生起一堆火来取暖,见到晶晶畏缩在角落直打寒噤,于心不忍,便叫晶晶过来烤火。晶晶犹豫了一阵,羞怯地挪到了火堆旁边。湿透的衣服让他们感到刺骨的寒冷,连连打着喷嚏,这样很容易生出病来。亮亮想了一阵子,取来几根木棒搭了两个架子,把湿透的衣服挂在架子上,并形成了一道布帘,遮挡了晶晶的视线。晶晶迟疑了片刻,也脱了部分湿衣服晾在另一个架子上,以便快点烤干。
两人在火堆旁瑟缩着身子。突然,一道凌厉的闪电伴着隆隆惊雷击进庙里,把破庙里的大香炉都击碎了。两人骇然地惊叫,不约而同冲破屏障,相互倚靠着壮胆,两个几乎赤裸的身子跌撞在一起。雷鸣闪电不断,两人忘了羞怯,身体由颤抖到炽热,很快便在暴风雨中的破庙里融为一体。
没多久,晶晶肚子便微微隆了起来,见不得人。在父母的拷问下晶晶哭哭啼啼地说出了和亮亮在山上破庙躲雨的那一夜。刘旺一听,脑袋都像被炸开了,刘旺的妻子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夫妇俩关起大门埋头盘算了一天,左右不是,只好硬着头皮找到黄柳家。
黄柳夫妇见到刘旺夫妇感到愕然,四目相对,尴尬而羞涩。刘旺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黄柳一听脑袋也像被炸开了,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儿子亮亮。亮亮嗫嚅着承认了事实。黄柳的妻子一听,捶胸顿足地哭喊:「造孽啊!」
黄柳是个通达事理的人,深知这事处理不慎就会害得刘旺家破人亡。二十年的恩怨,也是该解开心结的时候了。黄柳动情地说:「大哥,这一切都是天意,让孩子们尽快成亲吧,往后,我们就亲如一家了。」刘旺听后,热泪盈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一双大手紧紧握住黄柳的手。
自此,两家人便冰释前嫌,亲如一家,并且糅合了两家制作豆腐的技术和精华,将豆腐的质量推到了更高的层次。
又一个二十年,这座山走出了一个大美人,在省城开了家豆腐作坊,做的豆腐清润滑嫩,成了远近闻名的「豆腐西施」。
(作者为广东肇庆怀集人,文学创作三级。二○二○年上榜中国作家网「每周之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端砚●文河子
不知道一方泥土凝固成石头
需要经历多少沧桑和煎熬
从石头升华成端州一朵紫云
是不是消化了肇庆千年的底层苦难
和德行,才能在灾难深重的大地
脱胎换骨成为石头中的贵族
什么时候开始,石头深处窃窃私语
大小石眼布满血丝彻夜不眠
鱼脑冻、火捺、蕉叶白和金银线
各路仙颜云集,交头接耳
从老坑,宋坑,麻子坑和梅花坑
绕过西江汹涌的江底,翻山越岭
深邃的眼神若隐若现
偶尔以闪电和炸裂的形式
坦露隐藏已久的胎记
发布草拟了千万年的宣言
述说石头家族蜕变的真相
紫云升腾到人间
带来的是甘霖,沐浴肇庆的历史
滋润中国书画文化的墨田
从端州石工苦涩的汗水
到宋徽宗案头上的宣纸
包拯的正气到苏东坡的文才
都有端州砚石行云流水的足迹
砚石的千言万语一旦破译
就演义成肇庆民间不眠的灯火
和夜以继日的斧凿声
演义成劳工商人文人和官家的人生
砚石上的花草虫鱼和风物百相
与墨条清水之间滔滔不绝的絮语
打磨口传心授书画的经典
端砚,在文房中出落成谦谦君子
成为越写越厚重的肇庆文化
(作者原名朱伟全,诗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