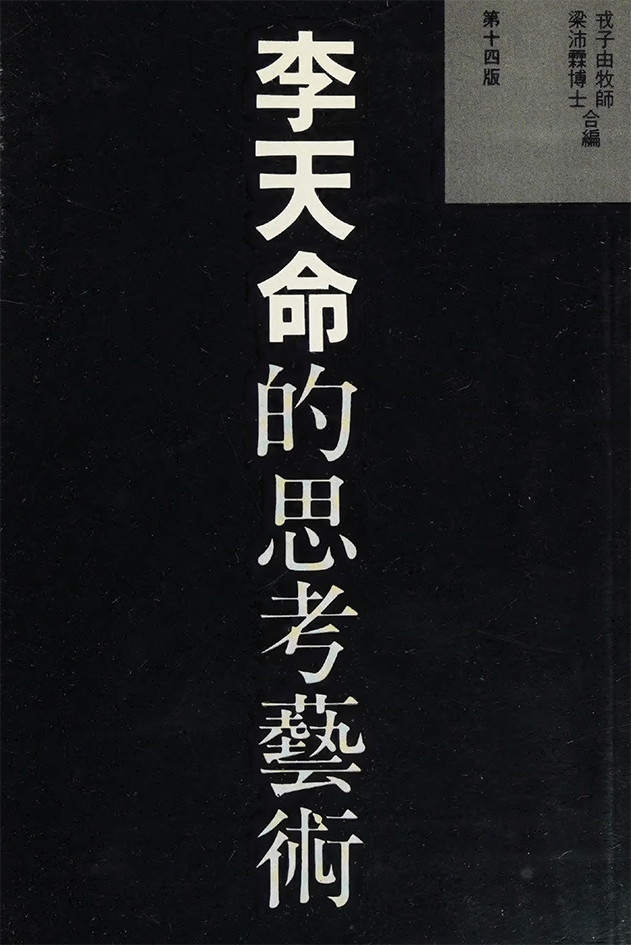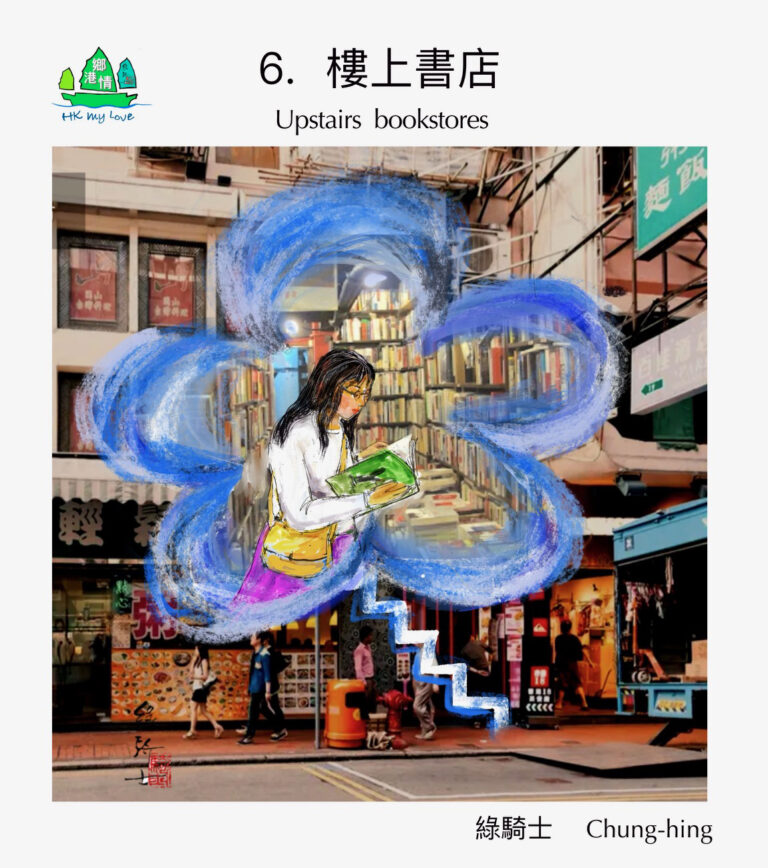编按:「文学是戏剧的灵魂,我以戏剧为主,同时兼顾文学,我的作品尽我之力,使两者融合……写作是寻找光的历程,我要在话剧这隐形或真实的四面墙中打开我的世界,在这里飞起来。」著名编剧家何冀平今年三月主讲「编剧与文学」,回顾成为编剧的契机以及文学对她的影响,内容引人入胜。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晚,「香港作家联会会员大会、春节联欢暨著名编剧家何冀平老师讲座『编剧与文学』」于香港北角简单而隆重地举行。
何冀平是享誉国际的编剧家,作品在国内外获奖无数。其代表作为电影《新龙门客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电影《投名状》、小说及话剧《天下第一楼》、电影《龙门飞甲》等等。
讲座由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罗光萍主持,在她情真意切多方位的介绍下,一身中式打扮的何冀平老师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开始了她的演讲。
寻找光的过程
主题演讲期间,何冀平回忆起自己成为编剧的契机以及文学对她的影响。她指出,很多人的第一步是写文章,而她的第一步是写戏剧。她忆述,儿时的她曾在一所平民学校念书,因为时常穿着父亲从香港带回来的衣服,有些与众不同的她曾遭受了同学的排挤和欺凌。这时,在机缘巧合下,何冀平读起家中的「莎士比亚全集」,这也是她最早接触的戏剧。她亦有提及就读过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开阔视野,以及周围同学对她之后写作风格的「终身影响」,她的创作风格也是「喜倜傥昂扬、少儿女情长」。
只听她将自己的创作历程娓娓道来——
文学是戏剧的灵魂,我以戏剧为主,同时兼顾文学,我的作品尽我之力,使两者融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寻找光的过程。
当年插队下乡落户当农民,很多人自此消沉。我其实可以不离开北京,但我自己销掉了户口,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我选择到了陕北,在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上,我突然觉得挣脱了一切枷锁,这里的农民不管我的父亲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也不管我是什么成份,我可以自由放松地做自己,这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想到弘一法师说的一句话:「褪去身上旧枷锁,方知今日我是我。」我是从那一时刻才知道,我是我自己。
当时的农村条件很差,尤其是在陕北。知识青年为了丰富业余生活,也为了村民们多些娱乐活动,嫌唱歌跳舞时间太短,撑不起一场晚会,于是我就开始写剧本。我不停地写,鐝头在黄土地上砍出一个土窝,坐下就写;棉花团捻成一个捻儿,做一个灯,埋头就写。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给乡民演我的小喜剧,打麦场上挂起煤油灯,就是我第一个剧本的舞台。后来油灯被大风吹灭,村民们想继续观看演出,就回家把过年才舍得用的马灯拿出来一溜儿挂在打麦场上,因为马灯有玻璃罩子,不会被风吹灭。后来我的剧作来到北京,走向香港,在世界许多灯火辉煌的剧场演出,我却永远忘不掉那一排打麦场上明亮的马灯。
我写的戏从陕北一直演到北京,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一个调令将我从西北调回了北京。那一年二十一岁的我在工厂当了一名工人,我还是继续写剧本,所写的剧本会在工人话剧团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现我是个可造之材,想要我去当编剧,那时刚好是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高考,大学开始招生,我很想去上大学,北京人艺的领导也十分支持我的想法。我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当时竞争很激烈,五千考生只收四十五个,我幸运地考上了。
两地生活的冲击
进入专业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戏剧创作,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了四年时间。话说回来,在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后,我回了香港一趟。之前我在香港的父亲并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因为十年时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络,父亲根本不知我的生死。在取得联系之后,父亲激动地将我迎回香港。从北京来香港探亲,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去松坂屋,去九龙城寨,我喝第一口可乐,喝第一口维他奶的时候,就觉得像在梦中一样。父亲因为高兴就天天请客,请的有香港朋友,也有台湾朋友,他们都很想知道何先生的女儿在大陆是怎样生活的?这一切的经历令我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我觉得自己应该将其写成剧本。
我的第一部戏《好运大厦》写的是香港一座大厦里发生的各个家庭的故事,毕业后我带着剧本走进了北京人艺这个话剧的殿堂,于是我成为了北京人艺年龄最小最年轻的唯一一位女编剧。 《好运大厦》公演时,买票的人们疯了一般,挤烂了售票亭,我想这并不是我剧本写得有多好,而是当时的人们太渴望知道什么是香港,香港是什么样子。
由《天下第一楼》到《新龙门客栈》
之后,我开始写《天下第一楼》,为了写这部戏,我用了三年时间,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第一步就去了烤鸭班。一进去,全是小伙子,而且都剃了光头。我就坐在旁边一张小椅子上,也没人理我,后来渐渐地熟识起来,我跟他们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
第二步就是开始去书中查找资料,这就是文学开始对我的戏剧创作起了作用。我将书中发现的中国文化的精粹都融入我的作品中,这样就将写老百姓的生活上升了一个层面,从没文化到有文化,从盘中五味上升到人生五味,我将平常生活里的烟火气写出了书卷气,我深知这里面有我心中的文学。
《天下第一楼》剧本完成后,我并不满意结尾,大概停滞了一年,为了找寻灵感写出一个满意的结尾。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看到了一副对联,当时完全就被它迷住了!上联是康熙写的:「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下联是纪晓岚对的:「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横批「没有不散的筵席」是我加的,这也是曹禺先生最赏识的一句。我将原句改成了「时宜明月时宜风」,因为我觉得我写的是一个烤鸭店,也写的是一个斗转星移的转换。这副对联一下点醒了我,我就把剧本结构变了。改成第一幕没有楼,是一个非常破败、生意不好的地方;第二幕起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楼,日进百金;第三幕反而是人去楼空,就用这样一条线把剧串起来,然后剧名也有了,而且这个结尾当时可以说感动了所有人。
《天下第一楼》公演后,可以说我是一炮而红,之后我为了家庭团聚移居香港。两年后,北京人艺到香港演出《天下第一楼》,徐克看完话剧后连夜寻人寻物,一是寻烤鸭,一是找何冀平。他说我有一个故事,您能不能帮我发展成电影?这就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部电影——《新龙门客栈》。我觉得自己唯一的贡献就是把一直青山绿水的港台武侠片的场景放到了荒沙大漠,而徐克非常喜欢这个场景。从创作电影《新龙门客栈》开始,我渐渐走进香港包括台湾的商业影视圈,在一班影视人中打滚儿。八年的电影电视生涯,时常手里有三个剧本同时进行,好像耍杂技,抛着三个球,哪个也不能掉下来。
文学戏剧的力量可改变命运
而我始终记得,戏剧是我的本行。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加入香港话剧团,重归舞台,第一部话剧《德龄与慈禧》深受观众喜爱,这也奠定了我在香港戏剧界的位置
在香港,一个文化陌生,完全不同的地方,我重新起步,我多了一个故乡,多了一片乡土。我想:我本身的中华文化,加上香港的中西文化,形成了我作品的语境和风格。
我的写作涉及舞台、电影、电视剧、戏曲、音乐剧,中港两地,一个个题材,要在错综复杂、堆如小山的资料中思索分析,找出一条路,如在黑暗中寻找光,直到看见光。
曹禺先生曾经握着我的手,追问《天下第一楼》我用来结尾的那副对联,我说,那是我对人生沧桑的感悟。
最好的结构是圆形结构。比如《红楼梦》,从哪里开始,回到哪里,最终回归本源。我在人生的历程中「寻找光」,把人生的疤痕化为光,我的经历和写作,使我学到很多,创作了很多,文学戏剧的力量改变了命运的无奈。
最近离世的立陶宛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说:「戏剧可以战胜死亡。」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学。当下的世界充满危机,愿用我的一技之长,给这个世界多一些温暖,多一点爱,这将是我一生的荣幸。
何冀平老师的话音未落,现场已是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台下认真聆听的作家及宾客们或满脸动容或眼泛泪光,大家都被这样一位享誉国际的剧作家真诚的生命历程分享而感动,正如何老师所形容当年北师大女子附中的学子们一般:「她们活泼不失大方,朴素难掩华贵……」从何老师身上以及言谈之中,我看到了这个时代所稀缺的那种朴素难掩华贵的真贵族气质。
回想起何老师所说的话:「写作是寻找光的历程,我要在话剧这隐形或真实的四面墙中打开我的世界,在这里飞起来。」
何冀平老师在戏剧与文学中的追光之旅,充满艰辛又光彩斐然,让人感佩,让人动容,催人自省,催人奋进。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作家联会理事。)

(香港作家联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