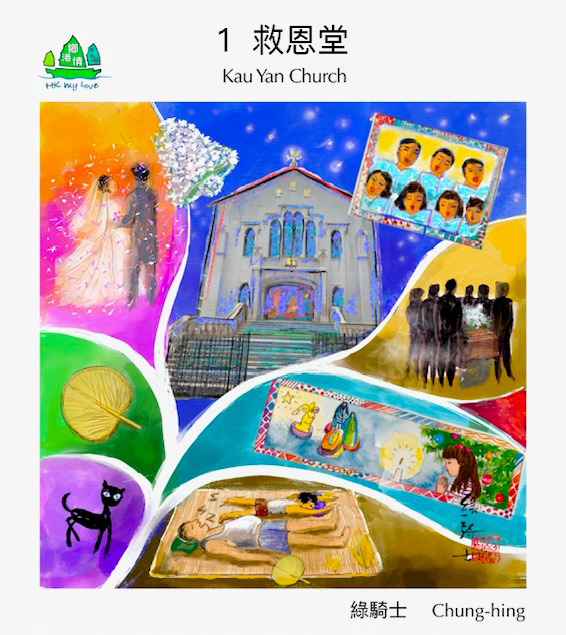近乡情怯●胡燕青
中国的文学史是包容的,即使说到人品很差的作家也不因人废言。唐初的沉佺期和宋之问,史称「沉宋」。因为近体诗规格发展到他们手上,几乎定调了。 《新唐书》说他们还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且都做过谄媚或贿赂奸佞小人等坏事,后人耻其言行。
《新唐书》写宋之问的八百多字,大都在骂他,不过也告诉我们他本是个天才少年,大概二十岁就已得武则天的赏识。并且「伟仪貌,雄于辩」,后来唐中宗把他一贬再贬,他来到浙江绍兴做越州长史,即地方官的秘书。唐睿宗即位,更恨他狡猾险恶,再把他贬到广东省去。
今天广东省真正富可敌国,但当时岭南地区乃「蛮荒」之地。长安人大都有「恐南症」,认为只要在南方呼吸或喝水,必定会病倒甚至死去。因此有传宋之问从贬地逃至襄阳,再从那儿逃回洛阳,过程中需要渡过汉江,因而得出了这首名为〈渡汉江〉的名诗: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诗里的「怯」,不知内容指什么。怕被人看见他北回?怕家乡的人不认他?总之,「近乡情怯」成了国人都懂的成语,这个「怯」正是用来做填充题的那个洞洞。回乡时,有人会觉得羞愧,有人会觉得内疚,有人会觉得自己老得面目全非,有人会不敢见某个他开罪过的亲友。这首诗非常易懂,不是《新唐书》说的「靡丽」、「锦绣」,而是具体、深刻而真诚的。
可是,《新唐书》没提此事,反而说,他和一个皇亲因太过腐败而被处死于桂林。是以有人说此诗不是宋之问写的。无论怎样,我们就诗论诗,这个作品非常有效地表达出「客旅」的处境和感情。首句描述陌生可怕的空间和它带来的焦虑、牵挂,一下笔张力尽显,第二行写时间在客旅期间变得漫长难熬:只不过半年,就要用上两个动词(「经」、「历」),再加上这个「复」字,有力地强调了他天天都活在痛苦之中。第三句是虚写,用上了形容词「怯」,让人先猜想「怯」的因由,而「怯」的具体表现就是「不敢问」,用笔大刀阔斧,情感却藕断丝连。我觉得此诗实在写得极好,不仅精准有度,朴素自然,感情体会深刻独到,还留给读者参与的空间,甚是耐读。
(作者为香港作家。)
对抗能力●张欣
生活本身就是骨感、无奈,就是你需要什么就没有什么。
比如我们辛苦为文你们就说是烂鸡汤,那我今天就写点茅台。什么是对抗能力呢?就是你对现状极端不满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那就不是一个认知问题,大道理小道理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人性是很顽强的,有人从小吃伤了南瓜,无论多有营养一辈子都不再吃南瓜就是明证。所以不要讲道理。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自己的对抗力。
有一个朋友在药房工作,每天都是对着药瓶子摆药发药很烦,但是他每逢周日会去自主的小乐队吹小号(在家也不能吹邻居会烦),我的朋友许石林就是去文化馆唱京戏,噢噢噢的拖腔拿调,他的优点就是比较达观。
有的人是读书写诗,有的学昆曲,有的是旅游或者做菜、烘焙。
把爱好变成对抗力肯定是一个办法。
我有个朋友她妈妈就是爱抱怨认为全家人都对不起她,我的这个朋友绝对不讲道理,直接带妈妈外出游玩,去五星级酒店享受美食与服务,她妈妈就比以前心平气和多了。
所以,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一个台阶也可以加强对抗力,因为你会觉得如果我不辛苦工作就没有眼前的一切。
有朋友说,我也每周去合唱团唱歌啊,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可是还是深陷现实的泥潭拔不出来,内心有着深深的厌恶感,但是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逃离。这种情况就是你的对抗力太弱了,无法招架对现实的巨大不满,也是许多人荒废了自己的重要原因。就是如果刷刷手机,看看热闹吃吃瓜,再跑到别人的生活里混一混时间也是好打发的,但是通常结果是更深的埋怨和虚空,感觉时间如细沙般流失,自己仍旧两手空空。
这个情况就必须找到深层次的目标,你看沉从文研究服饰,他那么爱文学又那么有才华但是又不能写作,这种苦难不可谓不深重。
然而他研究服饰如此博大精深,令专业人士都不得不佩服和感叹他的能力、耐力以及对细节的钻研。这就是他身上了不起的对抗力,就是你把我碾成灰我也能从中开出花来的能力。
人,就是这样,没有人会重视你怜惜你,共情于你内心深处的悲伤。别作梦了,没有。只有自己摸索着找到出路,然后用比工作辛苦百倍的努力走下去,一直走一直走,才能真的不介意眼前的苟且。
(作者为广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永恒的一瞬●风歌
鸣蝉嘶嘶
阳光在摇曳的叶间飞舞
重认柔风
多少年前窗畔读书声
纸笔摩擦之间呼吸着满眼山野绿影
传来的微热香气
梦想在无限飞翔
白云下无限生趣
踏上高楼作为师者
听着操场上的嬉戏喧哗
共鸣的青春
河岸远映帘外晴空
纯粹初心激情高昂
缘份是你我约定的——是非题?
荔枝园内星空巴士
银光手环一双说永远
长洲咖啡南丫岛豆腐花
日记簿上留下可爱
九份山城十份幸福
铁轨升着良愿天灯
密密麻麻真心诉说
火心炽热盼神看顾
那
徘徊于一瞬
与永恒的
那些年
(作者为香港青年诗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