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五月二十日,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明清研究中心特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陈炜舜到校,以「浅谈战后香港大专院校的诗词写作教学」为题,纵论一九四五年至今,香港古典诗词教学的源流嬗变。本文为演讲精华。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明清研究中心特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陈炜舜老师,莅临中央大学文学二馆,以「浅谈战后香港大专院校的诗词写作教学」为题,纵论一九四五年至今,香港古典诗词教学的源流嬗变。是次演讲,由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明清研究中心主任李宜学老师主持。
庠序起新风——诗词写作教学简史
诗选与词选,是现今大专院校中文系的常规课程,内容以古典诗词选授、习作训练为主。但诗词课的由来,乃至诗词教学的发展脉络,可谓知之者甚少。陈老师指,谈论诗歌创作的历史固然悠久,自唐到明清,不乏诗法著作,惟论述流于技术范畴,较为零碎。直至民国时期,西学东传,学者整理国故,诗词也因去古未远,热衷者众,不少谈论诗词作法的著作因而问世。兼之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学文学院召开文科课程会议,讨论如何设计中文科课程,诗选、词选课程由此滥觞。其中最早呼应北大的,当属谢无量的《诗学指南》、《词学指南》,流传于坊间,属于补充读物。而院校内部,讲授诗词的老师,则各自撰有教材,如北京大学黄节的《诗学》、东南大学顾实的《诗法捷要》、大夏大学冯振的《七言绝句作法举隅》,皆为课堂讲义、教材。甚至喻守真的《唐诗三百首详析》,如今仍见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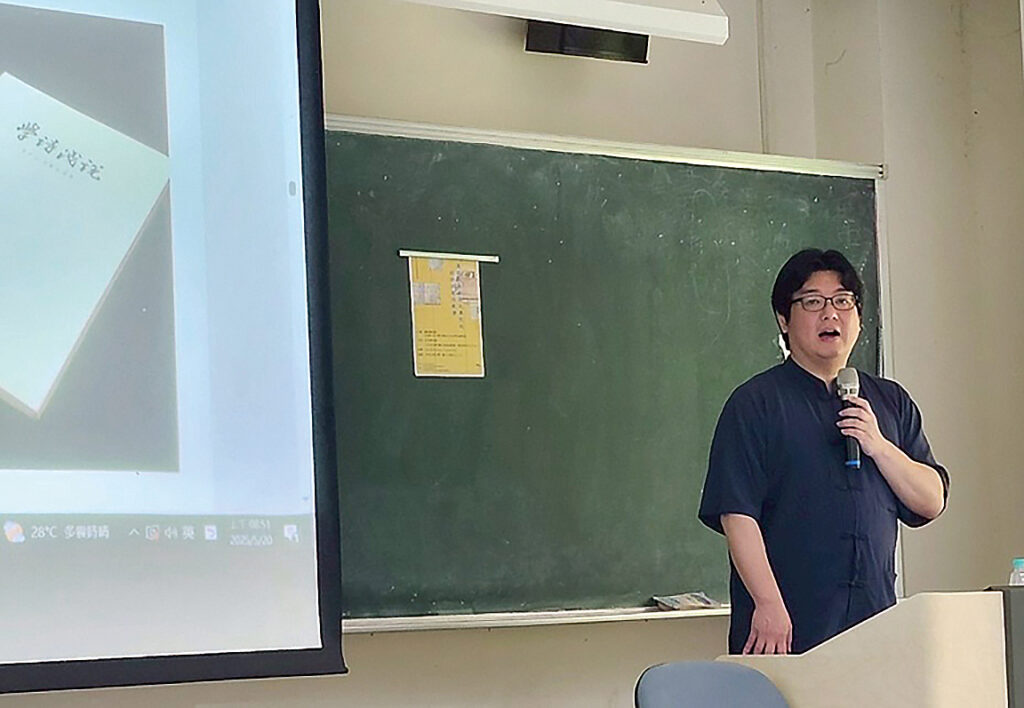
至于香港的诗词教学,情况相对复杂。香港作为曾经的英殖民地,一度是酝酿革命的温床。惟民国建立后,不少清朝遗老南下幽居,又香港开埠以来,商业发展带动文化繁荣,受之影响,诗词风气仍炽。陈老师并提及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罢工,称在民族主义、左派思潮影响下,英国统治者对时局不免忧虞,时任港督金文泰认为,要想保持香港治安,应加强中国的传统教育,于是接纳官绅建议,成立官立汉文中学,又延请前清翰林赖际熙、区大典、温肃等进驻港大。不过,赖、区这类旧式文人虽然工诗,却视之为小道而推重经史,因此这一时期的诗词教育,仍处萌芽之初。
虽然赖、区等对诗词兴趣平平,但赖氏的学生李景康,颇能在诗词教育方面有所建树。他深知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决意将之纳入政府管理体系。一九三○年代,李氏在汉文中学师范班之上,设置「诗选」科,复与叶佩瑜合纂《七言律法举隅》,陈老师认为,这大概是香港古典诗新式教学的第一部教材。可惜的是,战后汉文中学经历改组,师范班取消,《七言律法举隅》也无用武之地。但无庸置疑,这是战前香港诗词教学的一次重要尝试。
金针度与人——战后香港诗词教育回顾
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不久两岸分治,大批文人学者南下,他们与李景康同属一代人,接力推动战后香港的诗词教育。其时本地人口骤增,几所大专院校,如崇基、新亚、联合等相继成立,颇乏师资。诸如黄华表、易君左、郑水心、曾克耑、熊润桐、王韶生、涂公遂、钟应梅等人,过去就读或执教于内地大学,遂将新式教育观念带入香港,使诗选、词选纳入中文系必修。当然,各所院校对诗词教育看法不一,如港大虽有刘百闵、罗忼烈等巨擘坐镇,讲学仍以作品赏析为主,诗选一向并非必修。而其他院校,则相对重视诗词写作。尤其七十年代后,香港中小学已不教授诗词格律,大学生在缺乏基础知识、训练的情况下,旋即修读诗、词选,乃至做研究,进益有限,更不能彰显中文系的专业。故大专院校讲授诗词创作,实肩负诗教传承的重要责任。当年不少学生,至今依然缅怀先贤授课的情形,陈老师转述其中一二,谓曾克耑执教新亚时,会布置课堂作业,即席创作,题目不乏咏飞机、电话等新题目。又,曾氏讲课虽未必动听,但他为学生改诗,认真仔细,颇能化腐朽为神奇。
当时香港院校诗词教学选用的教材,大多为民国初年著作,除上文提及的几部外,尚有邹翰飞《作诗指导》、谢无量《诗词入门》、张廷华与吴玉《学诗初步》、游国恩〈论写作旧诗〉、瞿蜕园《学诗浅说》等。陈老师指,相较而言,居港学者专门撰写新讲义的情况则不多,其时或选用同门著作,或整理早年论诗文字。前者如曾克耑,以桐城门下,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为教材。后者如郑水心,以一九五四年《新希望周刊》连载之〈诗钟全貌〉作为任教联合时的教材。陈老师认为,余下堪称完备,只有何敬群于一九七四年编纂之《诗学纂要》,这是一九四五年以来,香港院校学者的第一部旧诗创作讲义,内容以介绍诗歌渊源、声调,与唐宋诗选读为主。至于词,因形式较诗复杂,其时教授入门著作亦多,如郑水心于学海书楼主讲之〈词概:起源体裁及其作法〉,连载于《华侨日报》。而有「女中稼轩」之称的陈璇珍,除在《华侨日报》发表文章,亦透过香港电台讲词,题为〈词学漫谈〉。另外,钟应梅有《蕊园说词》、何敬群有《词学纂要》,并以谢嵩《诗词指要》为此三十年间最后一部诗词论著。

陈老师总结道,这时期香港诗词教育,由南来文人主导,除在学院授课,他们亦广泛结社,带动民间创作风气。此外,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重视时间效益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追求「速成」,成为香港诗词教育有别于民国教学法的显著特征。最后,报刊、电台这类媒体,也对诗词教育的推广贡献甚多,且这些材料,至今仍有待整理,颇具研究价值。
一九八○年以后,随着老辈凋零,社团活动萎缩,新纂之诗词作法著述亦见少有,仅以顾植槐《简易诗法》较为知名。惟后生晚辈,仍以其他方式,宣扬古典诗词创作风气。陈老师提及其老师何文汇,多年主持全港公共图书馆诗词比赛、新市镇律诗、对联比赛,向社会大众积极推广古典诗词与粤音文化。何氏作为诗词声律研究学者,亦透过比赛,加深创作者对诗词格律的重视。过去如李景康、何敬群、郑水心等先贤,对诗律拗救的认知或存在偏差,如今可谓「后出转精」。至于陈老师自己,则从当年的参赛者,变为评审。虽然坊间或批评评审年年相同,入选作品甚少新意。但他直言,比赛并非纯粹比拼才艺,尤其对于学生而言,透过入围面试、即席对联等互动,考验作者,更具有深层的教育意义。如今,香港的诗词传统仍得以维持不辍,实应归功于此。
(记录整理者为璞社社员、本版特约记者。)
【学苑春秋‧师说师文】■ 痛

从痛到通
●新会商会陈白沙纪念中学梁璇筠老师
在篮球场上,不小心「笃鱼蛋」了。所谓「十指痛归心」身体上一点锐痛,便如针行于血,顷刻周身不舒服。甲骨文的「痛」字,如病榻之上汗珠滚落之形,一人卧于床,痛得出汗,细看真的绘声绘形。痛楚袭来,何曾容你只割舍那小小一块?
然而,解痛之道,竟也深藏于这古老的笔画之中。在痛里头的「甬」字——它本是青铜巨钟的悬柄。试想像那洪钟被撞响之时,声波就经此「甬」柄传导,方能沛然震动,声浪如潮,充盈整个空间。那是一种贯通无碍的力量。
奇妙之处在于,「通」字︰正是「辵」字以「行走」载着「甬」字而成。这便如同一艘轻灵的小舟,载着那根能传导洪钟巨响的柄,开始破浪前行。当「痛」的细针又要钻进生活里的某个缺口,我们需要的,正是按下那个内在的「甬」之按钮,启动那寻求通达流转的航行——舒筋活络,通则不痛了。
至于精神上的痛苦,像偶然不小心接下那甬柄,心魂之处那戚戚便弥漫思绪,辗转反侧,有时更甚于肉体之苦楚。这时默想身心如一,同样以「穷则变,变则通」的方法对应。海纳百川才能让心之小舟通行;甚至思考历史贯通古今,从前人「痛苦」经验中辨识路标。如活水,如行走,柳暗花明,不为一时一地之困境所滞。看开一点,以叩击心灵的甬柄;继续行走,才能驱动那载甬之舟的风。
如此看来︰痛是淤塞的泥沼,通则是载着钟柄的小舟。按动那名为「甬」的按钮,让寻求通达的意志之舟启程。无论身之淤塞,抑或心之郁结,愿以此「通」字为渡,轻舟虽时转孤屿,回看已过万重山。

评鉴之痛
●香港中文大学潘铭基老师
韩愈说,为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唐代人的想法。在学校里,究竟谁是当家作主的,是老师,还是学生呢?在大学里,课程完结时会有一份名为教学问卷的材料,让学生填写,以评鉴课程和老师的表现。从正面来看,教师在收到评鉴结果后,便可以据以改善课程设计,以及自身教学的表现。有不足者便加以改进,止于至善,莫过于此。
检讨大学教员的表现有三大方向,一为教学,二为研究,三为服务。研究可以量化,服务也有清楚的指引。教学的依据是什么呢?那便是教学问卷里的两道问题,一是对课程内容的满意程度,二是对任课老师的满意程度。
可以先撇开课程的满意程度,毕竟这是针对事而不针对人。学生上课,抒发对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是否满意的感受,十分合适,也无可厚非。但对任课老师的满意程度,便显然是针对人而不是针对事了!
设计好课程内容,在教学时认真准备,教学时因材施教,在「课程内容」已经可以全面覆盖了。老师本人要令到学生满意,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么学生便是教师的老板了!
于是,老师都不敢斥责学生。早上八点半的课堂,到来的学生往往未及半数,然后在往后的一小时里,学生鱼贯而至,好不热闹。按常理,面对如斯场景,老师当予以警告之词。可惜的是,教学问卷还在学生手上,那道「对任课老师的满意程度」的问题又显然是对人不对事的,如此困境之下,绝大部分教师也只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
多年前有一位台湾学者来访,系里安排了在我的八点半课堂让他做演讲。我心里想,学生如潮水般前来,多么失礼,也败坏了香港的名声。心生一计,求学说白了也只是求分数,于是安排了当天八点半来个小测,在九点才邀请该学者莅临。结果当然是美满的,学生精神抖擞,准时入座,台湾学者深感香港学风醇正,学生准时上课,提问踊跃(当然也是事前已作安排的),甚感欣慰;却不知他们只是为了应考而来。
视学生为顾客,或以之为老板,冠冕堂皇来说,名之为「学生为本」。在教学之时,究竟是老师要为学生的好,然后制订教学内容,还是跟学生详加商议,从而调整教学方针。何者为是,言人人殊。老师不必高高在上,但学生也要尊师重道,免却了为师的痛苦,学术才可得以承传下去。

隐隐痛
●显理中学曾咏聪老师
医生时常要病人形容痛感,若描述含糊不清,更会要求病人以程度区分,十分为满分。这方法非常务实,让抽象、难以比拟的主观感受,镶嵌在一把有刻度的量度尺上:十分要即时处理,七分就持观望态度,两分吗?你就多等一会,外面还有一群六分的叫苦连天。还有就是责任问题,痛的程度由病人打分,医生大可以安坐电脑椅,把头枕在双手上,指自己只是对症下药,原来你能这么忍受痛楚?我真是佩服!
但一分的痛感,是否就不用即时处理,让时间静静治理就好?若痛感一直蛰伏体内深处,偶尔爬出来刺一下,开怀大笑时又刺一下,提醒宿主,你是不应过于快乐。
去年送别一群毕业班同学,他们全修读商科,语文一环尤其羸弱,我拉牛上树,才勉强让他们完成一篇符合字数要求的作文。然而曾收到学生T一篇作文,真人真事,让我动容,每每想起也隐隐作痛。题目是二○二三年文凭试题目「一次令我百感交集的聚餐」。
内容忆述中四最后一天上课天,某同学宣布往海外升学,而身为班主任的我,允许他们到我新居天台烧烤,作为欢送。那天我们相约坑口,同学逐一现身在地铁站,全员到齐后,我才道出其中一位同学需要居家隔离,T心里已觉遗憾。买好食材到埗,我请他们先到室内休息,T自告奋勇,率先到天台张罗,安顿好再请我们上去。学生来来去去,开门关门。我们聊天、玩桌游,没有人发现T正默默烤肉,放在一边让我们随时享用。文章里有一支节,是他某次抬头,竟发现天台剩下自己,所有人都不知所终。
活动后我送他们到巴士站,着学生回去后在群组「报平安」。学生鱼贯上车,T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同学一个接一个离座,直至将要退学那位也站起,彼此交换一句「下次见。」便下了车。余下就只有自己。 T回到家没有在群组回覆,而是私讯班主任报到。我这才发现他的心意——希望聚会永不结束。
无数微小的痛充斥文章,没有直接抒情,因为快乐下卑微的痛,已布满全身,隐隐作痛。毕业那天,学生说起未来,T说:「我想往后再没有这三年过得如此快乐。」又一次无声的鼻酸。只是那时他不知道,留学他方的同学总在假期回来,而我千叮万嘱T要在公开试重写这题材,他突然乱写一通,最后中文不合格收场,才让为师感受到十级痛楚。

古早味的走马灯
●香港中文大学吴琪琪
家乡的古早味是舌尖上的走马灯,转一圈就少一味。那一年踏进城隍庙,海风裹着油香扑面而来。
糖房街的甜味是有形状的。花生汤老板舀起浓稠的琥珀,汤汁缓慢滑落,冲进土鸡蛋里瞬间开出蛋花。碗底的芋块吸饱甜汁,柔软得像年轻时的心思,轻轻一挤便渗出糖水。
转角那家芋圆铺,老师傅刨芋丝的手势快又准,汤锅掀开时,白雾里浮着肉馅的轮廓,剪开的芋包淌出白色的骨汤。花生糖碎落在上面,像一场金色的雪。
城隍庙的香火是另一种味道。朱漆供桌上的三牲五果堆成小山,金纸燃烧的青烟里飘着檀香枝的清香。穿碎花袄的阿嬷拜得虔诚,发髻上的银簪随着叩首轻轻摇晃,落在橘子皮上,微弱却耀眼。
这些味道都在消失。就像老街骑楼的彩瓷一片片剥落,像鱼贩铁盆里银光黯淡的带鱼,像手工润饼皮上的焦斑,再难复刻的火候。
我站在城隍街的废墟前,钢筋刺穿骑楼的腹部,挖掘机的轰鸣盖过了记忆里的叫卖声。回想去年此时,花生糖的甜香还缠绕在糖房街的晨雾里。
原来,所谓古早,不过是时光在心头尖上轻咬了一口,留下又甜又痛的牙印。

疼痛如砺,许生命如诗
●澳门培正中学曲书颐
夜里,小腿忽然抽筋了。
那是一种隐秘的痛,肌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缓缓绞紧,感觉像从骨头深处渗出来,并顺着筋脉蔓延,怎么也甩不开那股钝钝的疼。大人们总笑着说:「是抽条呢,好事。」可没人告诉我,长大原来是一件带着隐痛的事。
青春的敏感,像一场漫长的阴雨天。照镜子时,总觉得自己的脸不够好看,身材不够匀称,说话不够伶俐,举止不够从容。那种难堪,真像一把钝刀磨着血肉,让人坐立不安。
后来,疼痛褪去,身体定型,却在皮肤上留下证据——生长纹。大腿外侧、膝盖内侧,甚至是腰际,淡银色的纹路像河流的分支,蜿蜒在皮肤上。它们不痛不痒,只是沉默地宣告这里被猛烈地撑开,记录了那些沉默的夜晚,以及无声的痛。
直到我在社交媒体看到一个女孩。在意大利午后的海滩上,她穿着清凉,阳光吻过双腿的银色纹路,在地中海的碧波间闪闪发亮。我私信问她,她却回覆我:「它们不是裂痕,是河流。以前总是遮遮掩掩,可它们正是我们成长的证明啊!」
我终于发现,原来真正的成长,不是摆脱所有疼痛,而是学会与伤痕共处;不是成为完美无缺的人,而是有勇气面对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生长纹,是岁月的勋章。它们证明我曾勇敢疼痛过,却依然选择如河水般肆意流淌,像大树般昂扬生长,似诗歌般盼望远方。它们让我意识到:我只是我,我就是我,一个特别的我。

消散过后的痛
●显理中学丁加文
「痛」:部首为疒字部,也或许是由古人流传下来,「痛」是难以承受的。 「痛」是急性的、短暂间歇的、浅表的、热灼的、开放发散的、尖锐的疼,我想人们讨厌它,我也不例外。
由我有记忆以来,痛是身体带出的警号。小时候顽皮得很,想像自己是什么有特异功能的人,不顾身体的限制,总是挑战身体的极限,尝试告诉身体,谁才是主人。可换来的却是在游乐园不带眼,猛烈地向前冲,撞倒栏杆、门牙离我而去、额头起包的疼痛。我哭闹着,但痛感并没有离开我,我知道哭没有用,我只是试图引起同情,那刻起我知道——「痛」,是坏人。
长大了,也许是我知道自己没有依靠,耐痛能力也高了。 「社会大学」教会我太多,看清社会,看清人类后,领会的又是第二种「痛」。那怕是血流不止也好,我的神经似是再没有知觉那样,告诉我,警告我,我痛了。
那「痛」,不知何时起,一直缠绕着我至今,那是开放发散,侵蚀着我的痛。是吃多少止痛药也止不住的,折磨得教人感到窒息的,每吸一口气,那氧气似是变成针一样,蚕食着肺部的每一处。止不住的眼泪,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汪洋,是试图哭诉着被这地打压的「痛」。但可笑的是,大家也在这极度痛苦、极度疯狂的地方如此痛苦地活着,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一份能对得住父母的成绩?是为了能活在这城的薪水?还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想不到,因为最可笑的是,我连幻想日后的一切都感到痛苦,我看不清未来,不敢去看,现实太过残酷,我只是想着明天也感到害怕,还有什么资格谈论未来。
我想被人在意,可我却总是把自己困住,我想自救,但现实给了我重重一击,我不配。为何我活着是想着为谁,为何我努力过后却失去自我,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情绪病」。对的,我生病了,也许是吃抗生素也好不了的一场大病,我想着让痛感一点点地唤醒我尚余的一点感觉,好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还能战胜那「痛」。
但,谢谢那痛,迫切地使我在这地成长,学会更多,也许往好的去想,这「痛」保护着我,教我比他人更早看透我现时拥有的一切,教我去珍惜仍然愿意和我走向未来的人,教我去努力感受快乐。

生长痛
●香港中文大学胡珮嘉
男和女,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我常常想。六岁,穿上纯白校服裙,妈妈柔软的手编出马尾,那都是校巴上的男同学头上没有的,他没有裙,他穿着像烟囱似的,名为裤。所以,女生是长发、男生是短发;女生是裙子,男生是裤子,我决定要这样分。
男和女,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我依然在想。十一岁,不知名的痛在滋生,从左边的胸口开始蔓延,其后化为膨胀,用一把刀将胸口雕琢出弧度,再之后是骨盆,被雕刻的痛楚从上而下。最后,血初次从两腿间流出,蜿蜒于大腿内侧,如蛇一样,缓缓而下,滴在瓷砖上,变成血红色的花。
「每天都穿上这个就好了。」妈妈笑着。原本自由的部位,长出新的骨肉,我将她们放进钢圈。 「每月都用这个就好了。」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包,藏起所有的血红,此后四十年,忍住每月定时收缩的痛,如常生活。于是,我的世界从此性别分明——每天都穿上这个就好了……每月都用这个就好了……某个器官每月在皮肤下扭动,疼痛,直到最深处……我寻找同类,与我共享疼痛的人。那里会有几百个我,再没有鲜明的分别。或许,我可以习惯被束缚的胸脯,我可以忍受子宫的锐痛,然后在很久之后,我学会和所有不自由平静共处,无视身体的疼痛,甚至去孕育。那时,我会是真正的大人。

永远不能忘记的痛
●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郭妍心
「痛」是一种警报,如手触碰到火的灼热就是痛觉。心灵的痛更是剧烈的、把人绞裂的,我认为世界没有永恒,痛苦却像无底深渊。
前阵子我到访梵高的展览,看到了他的一生。从「夜晚露天咖啡座」的热闹温暖、「星夜」的迷失癫狂,再到绘画田园的恬静温柔,使我感受到那些挣扎、坚持和不被理解,是多么深沉的痛苦。自责、绝望、孤单,最终都在「麦田群鸦」中解脱,梵高也悄然无声地自我了结。
我自幼也经历过各种痛苦,家庭破碎的痛、遭受背叛的痛、被抛弃的痛、懊悔自责的痛、不被理解的痛,还有麻木的痛。痛到极致是麻痹,身体如被电击一般,剧痛会震碎所有知觉把人掏空,灵魂便坠落在沉寂深海。我猜想上帝发明痛的本意是保护人类,就像触碰火时手会本能退缩。人类在面对承受不了的痛苦时,身体或心灵会启动保护机制,例如选择遗忘。
然而,某些痛是永远无法忘记的,我们只能带着它拼尽全力跛行。痛苦很多时候必须独自面对,我想那就是一种成长的痛,是灵魂的年轮,记录着每次成长的印记;是持刀的匠人,一刀刀剔去软弱,凿出灵魂棱角,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独立,更有经验面对问题和保护自己。即使很痛很痛,也不要紧,请好好拥抱那个还很痛的你,对生命惊人的韧性,致最深的虔敬。

灰烬危花
●显理中学陈羡贻
废墟上空飞絮着无名不安,暗沉气压仿佛下秒就压在我们身上,你摆摆手,转身离去,我蹲下身,从地上拾起泛黄的拍立得,内里人影已模糊不清,隐约看到的,只是情绪。
晨光照下课室,我看着你手握白向日葵,说这是永恒的象征,我歪了头,目光从你的脸移到花蕊上,嘴角不自觉上扬回:「是吗?我不知道呢。」毕业袍下摆在草地拖曳,心情也随着被牵引,叫嚣着疼痛,没理由来的疼痛。
回过神来,你站在我眼前粲然笑问:「怎么了?」我摇了摇头示意没事,你挽起我的手臂,微风拂过我的视线,你的声音在风中拼凑,重写,又随着丝流而去,我点点头——「咔嗒。」相机键轻敲在心弦上,似乎有些被缝上的伤口重新裂开,窥探着彼此,誓要探出个什么来。
我攥着相纸,道不出什么来只觉得闷得慌,我还是没忍住那句早就在心底重复、疑惑、练习的——「我们还会再见吗?」你一瞬顿住神情,片刻过后你莞然而笑,「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只是毕业又不是离开了。」
不,你离开了。 「当然会再见啊。」
对啊,这不是你说的吗?那为什么你现在这样看着我?那为什么我们的重逢会是这样?困惑、不解、愠恼充斥着我的脑海但不得不看着眼前人,白裙黑袍飘逸对比,眼前霓虹光灯恍惚,与记忆重叠,却不与回忆重合沉郁。
如果那年秋天蝴蝶不在山谷流连,湖面上的枯叶没有搁浅,我是否就能留住你,我的眷恋是不是就不会被流放?月光映着双影模糊手上的焦点,你叹息着撕下关系。
当意识到我们快要踏进人生十字路口时,必须直视离别和感受生命的伤痛。我在这片濒死土壤上谈论着荒唐的梦,最后只化作灰烬危花沉积在我的苦难。
我问一句作结:「会再见吗?」你淡然说道:「不会,再也不会了。」

痛的无辜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陈煌森
失眠是我高中三年的底色,严重时一周的睡眠竟不足二十四小时。那时人是离心的躯壳,仅靠抽抽噎噎的痛觉栓住。痛的坦露或许仅需等待与调停;也或许,是对教育压迫的自残式反抗。传统家庭擅长将痛楚翻译为一种道德缺陷——仿佛失眠只是懒惰的变体,偏头痛不过是畏难的借口。我被迫承认我的神经在叛逃,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懦夫的血。这种被迫的自我定罪,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诡异的容器,里面总有一个批判者举着「坚强」的火焚烧我的「软弱」。每每肉体忍不住烫而颤抖时,脑海总要高喊「忍下去!」我忽然惊觉——我既是刑求者,也是囚徒。
每晚,我势必要扮演熟睡的酒徒,欺骗明天的我有义务上学。然而宁静的黑色总是被痛戳破,显得格外清醒,我竟然追问了许多我庸俗一生不敢觉察的问题。为何学习必须是吞咽而非品尝?为何割下我自主性的血肉喂养集体的饕餮?讽刺的是,学校与父母十多年来的挤压令我远离书桌,而痛却让我爱上阅读,像在荒漠中舔舐自己的伤口,尝到自由的腥咸。后来我问:痛在恐惧什么?透过阅读与思考,我开始反问:这份根植于我体内的痛,它自身又在恐惧什么?恍然发现灾难化思维原来就是意识里潜藏着「考不上大学你就完了」这句话。
当我读到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事物本身并不直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来影响我们」后,我在某个凌晨忽然想通了:原来,痛本身也是无辜的。它并非敌人,而更像一个信使,忠实地传达了那个被恐惧所扭曲的系统施加于我的一切。

不懂得游泳的鱼
●新会商会陈白沙纪念中学黄喧咏
生活中总是会经历许多种痛,做功课被纸割伤的刺痛,跌倒时膝盖擦伤的肿痛,胃痛时的绞痛……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痛,只要忍一忍,等待它自然康复便好。可总有些痛不断地围绕着我,如影随形的,消失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像是游戏中死亡后看广告复活的角色一般,杀也杀不死。
每当压力来临时,那种感觉仿佛就像鱼跳出了鱼缸,躺在地上喘不过气一般,奋力挣扎却又无能为力,那种无法呼吸的痛苦无处诉说,也无法解脱。这种痛苦是无法与日常中那些碰撞出来的痛比较的。
我曾问过大人们:「成长是如此痛苦难忍的吗?」得到的回答却只是「这算什么!我吃过的苦比你痛多了……」人与人的痛苦可以比较吗?是我过于软弱了吗?此刻的我,是那条不懂得游泳的鱼,被一层一层的浪盖过,在那涌动的水流中溺水。
路还有很长,我有点害怕疼痛的滋味,但是没办法,成长也许就是如抽筋拔骨般疼痛吧!直到某天,当我能在没有水的地面上呼吸时,也许我已经坚强地长成可以随意说出「这算什么」的「大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