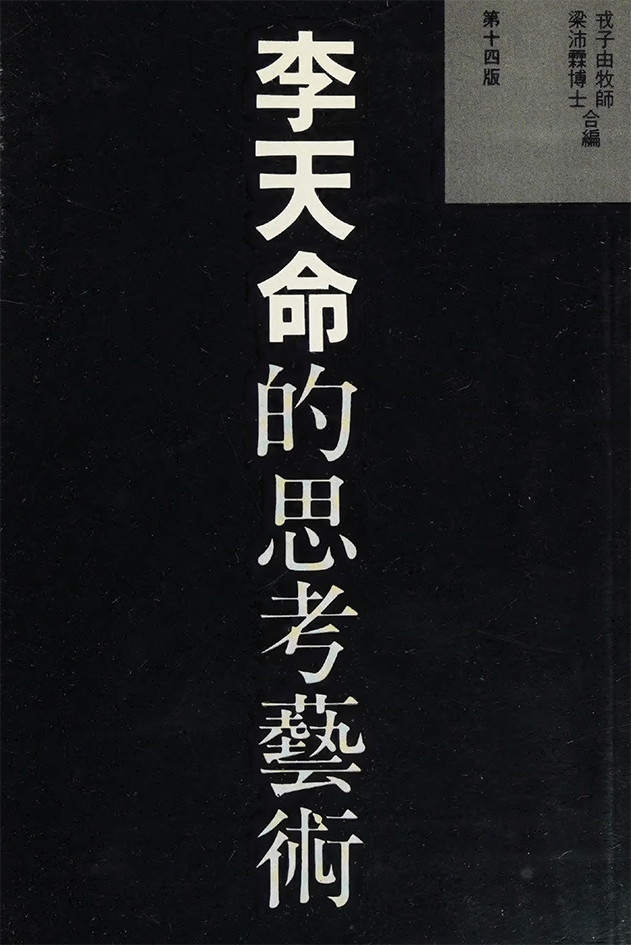邻居的树●胡燕青
在悉尼儿子家,邻居的老树是邻居的痛症,却是我的朋友。每一年到此地探访儿子,总看见此树越长越粗壮,占去邻居大片土地。澳洲的平房是连地买的(有地才让价钱够贵),买房子当然也得买下这树。
此树很大,树冠下的地足以建一个四十人教室。可是,这里没有教室,只有几个逐渐长高的小朋友。政府说这树是先存于房子的大自然生物,不能砍。这么一来,「祖母厢房」建不了,加个檐蓬也不容易。从用家的角度看,这真有点可惜。但从树和树的友人如鸟和虫子、甚至树脚下泥里的微生物的角度看,这是不作他想的美丽家园。
我不知道树的品种,只知道树很健康,树干极粗大,树枝疏密有致而且强壮圆润、树皮发亮,树叶均匀分布,而且叶叶新鲜,每一细节都显出树生长得极好,即使斜着长高,依然稳固平衡。一群大鸟住在上面,代代繁衍,就好像我们寄居于地球。只见它的枝条高低起伏,犹如江山布置,各为风景,各成文化,真是阴阳割昏晓;估计高枝日暖如赤道、夜寒为极地;低处则阴凉湿润,适合不同的鸟栖息活动,分头经营自己的故乡。从鸟蛋开始,他们孵化、待哺、成长、飞行,经历美丽的南半球的日出和日落,然后回到树里去,每一天变老,等一天离开。
我们仰头思考,却无法进入他们的童年、爱情和生死。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个决定。把树斩了多建一个厢房?让树留住容纳一个世界?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眷恋一个香港的小单位,和单位里刚上小学的孩子。而单位当然可以是一个厢房,或者一个鸟巢。和树相见多年,我见他越来越大,他见我越来越老。有一天我将再无力乘长程飞机到悉尼来,而树自当继续保护着这一群鸟。这友情将超过我们自己的生命。于是我为这一片相识的青绿命名:邻居的树。
一个下午太长,沧海桑田太短。人生的图钉曾把我们固定在彼此的身边,为彼此的小风景;这一切将飘荡于记忆的大海,为海洋不至于单调。
(作者为香港作家。)
流年忆旧——吃食堂●张欣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部队医院工作,当时的医院工作人员有两个食堂,一个是干部灶,还有一个是战士灶,两边的菜金补助不同,当然是干部灶高,战士灶又称大灶,菜金低,许多基层部队的大灶早餐也是大米饭配咸菜,因为没钱买面粉而且战士都是毛头小伙,一顿吃七八个馒头不在话下,伙食费就不够吃了。
当时我已经提干,所以吃干部灶。说来奇怪,明明我们干部灶这边的菜金高,但是伙食却不如战士灶,由于两个食堂挨的很近,大家出来进去的有时也会打饭到宿舍,发现战士灶应季的新鲜蔬菜特别多,还有红烧排骨、狮子头啥的,我们干部灶的炒菜里难得见到肉,豆芽炒肉那就全豆芽,沙葛炒肉那就全沙葛,实在叫人难以下咽啊。
一问,才知道战士灶虽然菜金低,但是战士们年轻、有朝气,尤其女兵多还会过日子,召集大家一起去捡柴(树枝、废木头啥的),当年的大锅饭大锅菜都是烧柴的,捡柴可以省菜金啊;他们还自己开荒种菜(基层医院都是在山旮旯里有的是地),浇水施肥长势喜人;同时炊事班全体都是战士,他们还自己养猪,你说那伙食能不好吗?
反观我们干部灶就一司务长骑个二八寸的自行车去农贸市场买菜,如果司务长一不精明二不贪污(通常贪污的司务长单位伙食好)买的菜简直让人一言难尽,不是过季菜就是又老又糠,还有干部灶炒菜的大师傅请的都是河南人属部队职工,手艺方面主要是会做面食、馒头、包子、花卷啥的,炒菜如果食材不行也难炒出什么花来,说白了就是不好吃。
后来医院后勤科的负责人也看着战士灶眼热了,说合灶合灶,一个医院搞那么多食堂干嘛,心里盘算着,干部灶菜金高战士占便宜,但是战士们勤快对于伙食有帮补两头都不吃亏。伙食肯定会比从前好。
结果并不是这么回事,两个食堂合并以后伙食更差了,为什么呢,因为战士们一看增加了那么多人,怎么捡柴种菜养猪都是供不应求就干脆躺平什么都不干了,那他们本来菜金就少,合灶就等于占了干部灶的便宜何乐不为。
隔了一段时间,两个灶又分开了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那时候就知道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容易眼红别人但其实又很难占到别人的便宜,所以对于趋之若鹜的东西常常抱以警惕。
(作者为广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薛忆沩的「小眼睛」与其文学内观●伍东林
薛忆沩的《小眼睛的小学生》远非一部简单的童年回忆录。在其看似个人化的叙事之下,涌动着的是一部以精微笔触重构历史、以内省姿态勘探心灵的作品。它既是作家对其文学原点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清晰地映照出他作为一位「深圳作家」所特有的冷峻、敏感与跨地域的文学气质。
小说的标题「小眼睛」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文学隐喻。它既指代一种生理特征,更象征着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不是宏大、全景式的俯瞰,而是聚焦、内敛甚至略带偏执的凝视。薛忆沩正是通过这双「小眼睛」,避开了历史叙事的俗套,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的大时代」溶解于一个敏感儿童的日常感知之中:入学年龄的困扰、宁乡「留学」的惶惑、样板戏台词的语言魅力、对死亡与追悼会的最初惊惧……时代的风暴在孩童的视角中被折射成无数碎片,它们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而是与个体的饥饿、羞耻、好奇与温情紧密交织的生命体验。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赋予了历史以可触摸的肌理与令人信服的毛边。
薛忆沩的语言以其精确和冷静著称,他书写苦难与荒诞,却极少宣泄情绪,而是以一种近乎解剖学般的耐心,将个人与家族的际遇娓娓道来。外婆对「双眼皮」的执念,交织着遗传的遗憾与时代的审美焦虑;父亲在「干校」的境遇,通过「一大勺猪油」的尴尬细节得以呈现。这种克制而饱含张力的叙述,使得文本的情感力量不是扑面而来,而是静水深流,在读者掩卷之后愈发深沉。这正是薛忆沩文学风格的核心:他相信细节本身的力量,信任语言自身的逻辑。
作为一位常被打上「深圳作家」标签的写作者,薛忆沩的文学之路与这座城市的特质有着隐秘的共鸣。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消解固着的本土,强调流动与重构。薛忆沩的写作,同样具有这种「离散」与「重构」的气质。他从湖南到深圳,再走向更广阔的国际文坛,其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往往也处在一种「在别处」的状态。 《小眼睛的小学生》中那个不断在长沙、宁乡、「干校」之间辗转的男孩,其心灵早早就体验了「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这种源于个人经历的「漂泊感」,使他能以一种抽离而又充满同情的目光审视故乡与历史,从而获得一种超越地域性的普遍意义。
从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写作至今,三十六年的文学历程,是一条不断向内深挖、向语言极限挑战的窄路。 《小眼睛的小学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文学矿脉的一次深度回溯。书中对语言本身的迷恋(如对地名、简称的思考),对叙事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探索,是他在《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等作品中更为极致的文学追求的延续。
总而言之,《小眼睛的小学生》是进入薛忆沩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它告诉我们,一位杰出的作家如何从最个人的记忆出发,通过卓越的文学技艺与深邃的内省精神,将一段特定历史转化为关于成长、创伤与救赎的永恒叙事。薛忆沩以其「小眼睛」的专注,为我们洞开了一个无比深邃而广阔的人性世界。
(作者为《深港书评》主编、文化记者。)
【创作园地】■
心形胸针、击中●舒非
心形胸针
轻巧一枚胸针
扣在胸口
三朵紫罗兰,由两片绿叶扶持
清楚记得购买自那间铺
维也纳大街转角处
傍晚下过雨
雨后天放晴
湿漉漉石板路斜斜往上
有家琳琅小店
你站在橱窗前
指着心形胸针
好靓
我进店就买下
嗯,就是这枚胸针
今天获得女诗人青睐
击中
她一下击中他最柔软部位
社会染缸混迹多年
天涯海角走遍
风浪里打滚
什么世面没见过
有什么人无接触
权贵有之
富豪有之
学者有之
名家有之
美女更是数不过来
可是偏让她击中了心扉
他的心并不全是冰冷
也有柔软一角
那一角跟文艺关联
年轻时代留下的印记
寻常看不见
触动心扉时
突然涌现
犹如神奇喷泉
水珠在阳光下钻石般闪烁
(作者为香港诗人及作家,曾任香港三联书店策划编辑。)
天眼仰看天外天●周蜜蜜
晨曦初醒,群山的臂弯里
盘旋石阵的棋盘
星座在铜栏上流转
引我们攀登,攀向天风回旋的垭口
在峰峦合拢的瞬间
巨瞳自天坑睁开
——四千四百五十块光年
正锻成银鳞,向深空铺展
悬空处,衣衫鼓荡如帆
山岳般寂静的钢索
正测量月光下蚂蚁的触角
把脉冲星的信笺,译成电波
当云幕拉开,湛蓝倾注
整座镜面浮升为时空之钥
那些行走在三角锋刃的检修者
多像穿越维度的光点
后来在球幕幽暗的腹中
射电流淌成宇宙的耳语
回望处,银轮在万壑间
每块镜面都盛着明天天外天——
天外天——这大地举向苍穹的明镜
盛满人类全部的明天
(作者为香港作家、儿童文学作家、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
香江娥眉洲之色●冷月
乙巳年七月十九,好友寄来在大埔拍摄的风景照云:「娥眉洲,位处船湾淡水湖之东北,被列入印洲塘海岸公园,乃潜水胜地。」因美景太美,与连日的黄、红、黑雨形成强烈对比,故记述之。
黄色的倾盆,
红色的警报,
黑色的瀑布,
黄、红、黑恍似苍天的悲嚎——
因狂放之徒而怒吼,
为受苦难者而悲怆!
蓝色的晴空,
白色的云朵,
绿色的山岭,
蓝、白、绿构成一幅文艺复兴——
天然绘制而无添加,
定名为娥眉洲油画。
黄、红、黑警报后,
有看得见的蓝、白、绿油画,
还有看不见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云霞,
环绕护持着这货真价实的东方之珠。
(作者为香港作家,着有《错失的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