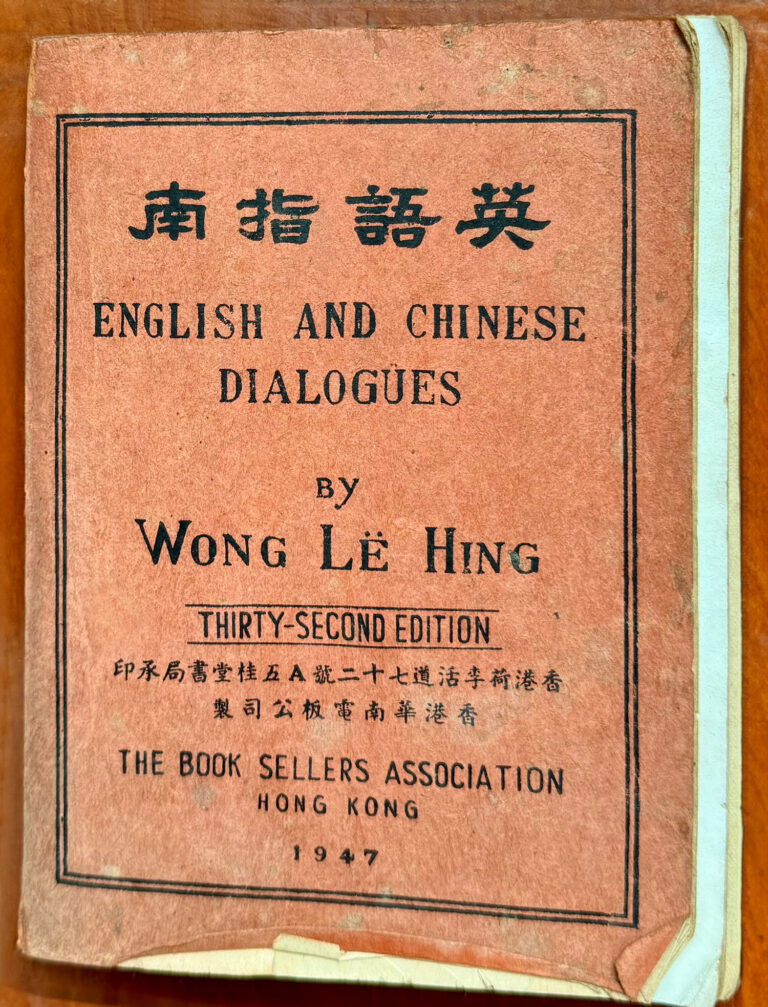走在林荫道 ●陈德锦
那年游杭州,走北山街,看西湖,沿街是密密罗列俗称「法国梧桐」的悬铃木。浓荫软风,步伐轻快,不觉已走到孤山和苏堤。听说近年因兴建新地铁支线,一些行道树都得让位。在林荫大道上漫步,岂不成为一种奢侈?
林荫大道,香港也有吧?港九各区的确有一些街道叫avenue。香港街道名称英式为主,主要叫road(道、路)与street(街),窄一些叫lane(里)或path(径)。若依字义看,富拉丁味的avenue是「两旁通常植了树的大道」,狭义是指「通向大宅的路」。但以九龙尖沙咀区为例,很多avenue竟然只是些小街小巷,像堪富利士道、宝勒巷、碧仙桃路、棉登径,却罕见树木,中文译名都不统一。可见心慕林园,也不能过份失实,所有这些狭窄无树的小路,大概只取狭义:通向大宅。然而当年的大宅今天早已成了一幢幢商厦。
以avenue为名,是否感觉上较为优雅?某些大型屋苑的内街,也以此为道路名称。太古城有,彩虹村也有。但真正有意识建成优雅街区的,可能要数葡萄牙商人梭亚雷斯(Soares)。梭亚雷斯是澳门人,他的父亲是南湾加思栏花园的设计师。上世纪初他向政府征得一幅何文田地皮,着手打造一个「花园城市」,为在港葡籍人建立一个小社区。几幢优雅的宅第坐落于火车桥旁,区内所有街道都叫avenue,包括胜利道、太平道、梭桠道、枣梨雅道、艳马道(后三街以他本人及其妻女名字命名)。虽然这「花园城市」早已不存在,也没有多少照片留传下来,但可以想像当年必然有花木绕道,居住环境不会像今天那么挤逼。
有树木排列于行道,似乎很接近自然,但树木也有生命,生命也有周期,年深日久,根脉暴露于地面上,常引致路人扭腿伤足,塌树的情况也时有所闻。除非每棵树都已划出足够空间,否则人树争路,亦非美事,可见林荫道路实在可遇不可求,有点奢华了。回想在杭州街道漫步,绿荫为我一直驱走暑热,竟又不知身在福中。
(作者为香港作家。)
PMU酒吧里的写作课 ●唐睿
吧台上横陈着几枚硬币,用手指并来并去,确实没算错,首天上班,一共就只有二元六毫欧元的小费。
店东A打了个哈哈,装出一副不无同情的样子,就用夹着烟蒂的右手,拉了杯凉得直冒汗的Stella Artois走进店的深处,在保安严密,有点像找换柜台的投注间,跟两位同事数点一夜的收入。
这路是不是选歪了?
在圣日耳曼大街旁的亚洲餐厅里,来替工的A把你拉到一旁悄声说,跑堂的潮州胡须佬,天天带着一帮同乡伙计跟日本总厨对着干,这餐厅迟早玩完。我的酒吧快将开业,你刚考上大学,正适合来当兼职。
于是你卸下了厨师服,披上西装马甲,站到有点年纪的橡木吧台后面,迎着威士忌色的水晶灯,徐疾有致地摇晃起手里的雪克杯。
可是,A却对你说︰「我们的店并不卖Cocktail。」
酒吧的门口摆着一台彩票机,在Porte de Bagnolet这个基层移民区,每天都有北非的老头和汉子摇摇晃晃走进店,点一杯咖啡,刮一张没有中奖的彩票,然后在柜台留下一两枚黏着涂层的角子。
「盯好这些Arabe,记牢他们喝了什么,喝了几杯,别让他们蒙混白喝,尤其是人多的跑马日。」首天工作,店东A这样叮嘱你。
跟香港的投注站不同,法国的赛马投注,都是在Pari mutuel urbain(PMU)的指定地点进行,一到赛马日,酒吧就挤满了抽烟喝酒的赌徒,一片烟雾弥漫。
站在吧台前喝的expresso一元二毫欧元、坐在馆里喝的一元六毫欧元、Café crème二元一毫欧元、un demi的Stella Artois一元八毫欧元,啤酒的泡沫不能低于杯上的刻度,否则客人有权退回叫你另打一杯。 1664和Leffe都有专用的酒杯;而虽然51和Ricard都是保乐力加旗下的茴香酒,但每天都来喝上一杯51的机车司机,和始终在喝Ricard的货车老板,是绝对不会对调口味的。
「你还管得了这些?那烂鬼都付清了酒钱吗?」店东A问。
那人其实并不烂,只是有点不幸,他没法让法国承认他的突尼斯医科文凭,结果只好终日留连酒吧,打听各种零工的消息。这样的故事,从前也听落难到九龙城的广州牙医说过,只是愿意放在心上的人并不多。
辞别酒吧的那个晚上,你将小费堆叠成一列币柱,然后请一脸狐疑的A,帮你兑换成三张十欧元纸币。该怎样向他说明,观察和倾听故事跟小费进帐的关系呢?直到掩上店门的一刻,你都想不到合适的说辞。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