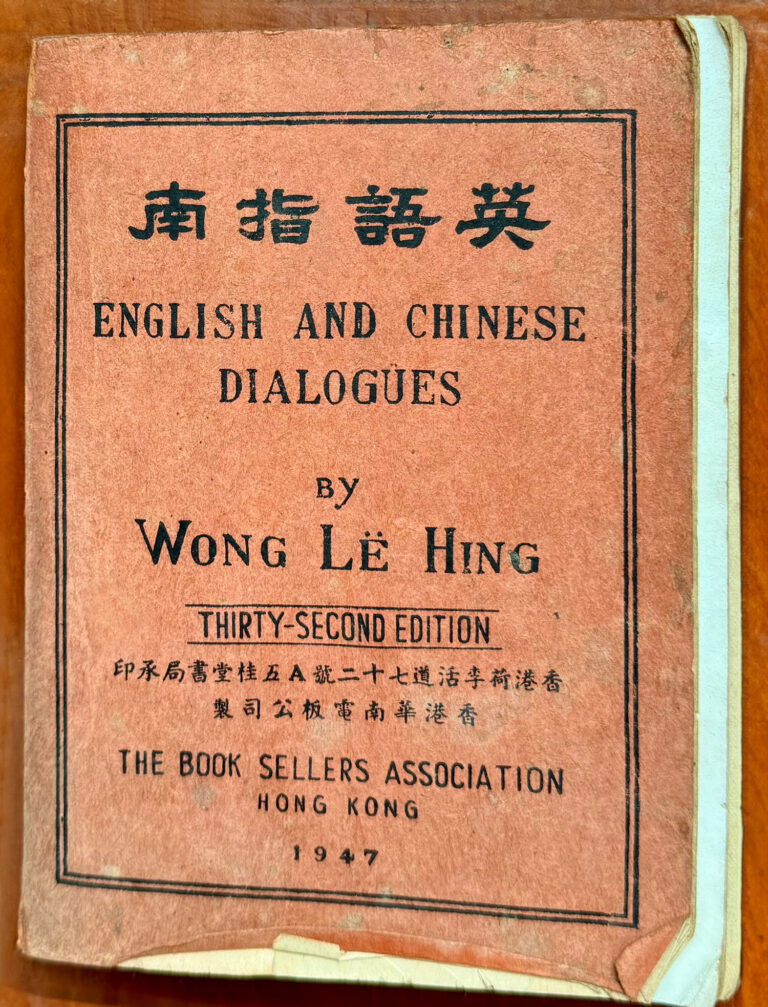编按:著名编剧何冀平的成名作《天下第一楼》,被誉为当代现实主义剧作精品,曾得文化部戏剧最高荣誉「文华奖」和中国戏剧文学「曹禺奖」等多项大奖。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后二○二二年十二月于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重演,反应热烈,作者从而忆起当年因此剧与人艺院长曹禺的因缘交往,同时侧写曹禺的人格魅力,以至他对戏剧艺术的坚毅追求,读之令人动容。
主编:潘耀明
执行编辑:张志豪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春天,窗外是北京那一年的头场春雨,我和夏淳、顾威两位导演来到「前三门」,那时候前三门是北京的高尚住宅,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住在这里。
大学毕业后,我被点名聘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编剧。曹禺是人艺的院长,但是很难见到他,只有开大会远远地看到他,可望不可及。我生性不大喜欢和人交往,尤其是领导,绝不会去赶着接近,好在我来的是北京人艺,这个不以人事关系为轴心,而看重本事的地方,否则可能永远不会面对面接近他。直到我写出《天下第一楼》。
真心喜欢并题写剧名、长诗
曹禺老院长的家十分简朴,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我熟悉的那种浅驼色镶边的沙发套,只有面对窗的一个书桌,古色古香。
他身体不好,长年住院,特意从北京医院回家来见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没想到我是个女的,还这么年轻。他让我和两位导演坐在沙发上,他拉了一把藤椅,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剧本,眼睛放着光。他说过:「读《茶馆》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读到好作品时的心情。」我不敢说《天下第一楼》是他眼中类似《茶馆》的好作品,但是我真的见到,他有些病态的黄白色面孔上那双眼睛闪着光。
剧本他看的很认真,谈意见时,他完全没有看过手里的剧本,情节细节以至台词都记得。他说﹕「喜欢剧本的结尾,看当中就想会是怎样结尾,没有想到会这样去结尾,最后这副对联用得好,上联是乾隆,下联好像是……」我答道:「是纪晓岚的。我稍微变动了一个字。」他点点头,接着说:「『危楼』这个危字,有两个意思,一是形容这楼之高,一是说这楼已经危险。完全切合这个戏的主旨。最欣赏的是这个横批:『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是这个戏最宝贵的一句。看剧本时,我就在想,这个剧本怎么结尾呀,没想到会有这么漂亮的尾声,一副对联,一个横批,就把戏完满地结住了。」他说,喜欢常贵,还有玉鶵儿,这个唯一的女角色,很有味道,她的下场会很好。剧中没有写到玉鶵儿之后的下落,直到多年后《天下第一楼》改编成电视剧,有了篇幅给人物,写到玉鶵儿时果然如此下笔,可见曹禺多么了解作者笔下的人物。
他对导演讲:「这是一个好本子,会是一台好戏,戏里有许多有意思有趣味的东西,看着看着就叫人笑出来。这个戏不能排得太严肃,太沉闷,要明朗活跃。」又被他说中,受那个正统年代的影响,初期排演过于严肃,但很快纠正过来。他给年轻作者的剧本提意见很慎重,即使不太喜欢,也基本上以鼓励为主,但他是真的喜欢《天下第一楼》。暮色渐浓,从下午谈到掌灯,曹禺依然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停不下来。
他主动为《天下第一楼》题写剧名,写了几张让我们选,还附写了一首长诗,这让所有人惊喜,他已经很久不写诗了──
你是泪水流下的水晶,
弯曲曲的,长长的,尖尖的,圆圆的。
想不出你是怎样形象;
却又像夏晨的露珠,
那透亮、水灵灵的,
满含无限的光明。
水晶中神仙给你刻出,
一朵玫瑰,红得像火,
那是你的柔情、温厚、善良,
一双魅人的眼睛。
你又是一支青玉的笔:
你画出多少人物,
常贵、玉鶵儿……
还有卑鄙、苦恼、愤怒,
画不尽的人性。
幸而你们都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你们有一天会是青天的神仙。
看!这不筑成那痛苦,
那悲与喜、善与恶的斗争? !
《天下第一楼》那昏天黑地的世界,
却又是清凉、洒脱的尾音。
「时宜明月时宜风」,
我们是风和月,一时是客一时是主人。
我羡慕你们,你们用玉笔
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
道尽世界的不平。
你那样美,却有鹰般的眼睛,
你爱、你怜、你恨,
渗透善良、可怜、贫穷与欺凌。
你们将是宇宙中永远闪光的星星。
至今,曹禺的手书依然挂在北京人艺的会议室中,每逢见到,我心头都会发热。
「写戏是清苦的,你要坚持下去」

剧院凡有新戏,曹禺喜欢在排练场看连排,与演员近在咫尺,和在舞台上看是两种味道。演他自己写的戏,曹禺会在观众席上看。曾经有一段日子,受外界影响,演员表演忽略个性直奔主题,表演僵化,说台词像讲道理。他在台下一边看,一边心里着急,嘴里不由说:「快,快点!」趁午休的空档,他给演员讲人物,人艺人都知道,他给午休的朱琳讲《雷雨》中侍萍的事。像他这样,给一级大演员讲戏,我可不敢,但这就是一个编剧,对作品的执着和着重作品呈现的不懈追求。

《天下第一楼》他连看了五遍,流了泪,他说「我就是常贵」。饰演常贵的演员,要演出曹禺心态的影子才算合格吧。每逢连排,作者要到场,剧院的一级演员,个个赫赫有名,大小头目全在场,我通常坐在最后,一声也不敢出。有一次戏演完了,他看见我在,招呼我过去,拉着我的手问:「你尚且年轻,哪来的这沧桑?」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不知道,因为我的父亲在香港,我从小就受歧视,我的沧桑是从六岁开始的。
《天下第一楼》没有辜负曹禺的赏识。首演后,连演一百五十场。之后应邀去了东南亚、台湾、香港、欧美。最有意思的是台湾和香港。这部戏,是中国大陆第一部话剧进台湾,台湾新闻局将剧本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审,没有找出一句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因为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戏在台湾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
再有是香港,这次在香港演出,我站在剧场里,百感交集。三十三年前,就是这个剧场,《天下第一楼》演出,台下的徐克导演,看完就到处找我,从写《新龙门客栈》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直至如今。
演员有句行话,刚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灾难。编剧这一行,上来就是主角,没有机会当配角,是福是祸,都得硬顶着上。
曹禺一生都想写剧本,最后一次是一九七七年。他想写一部四人帮迫害老科学家的剧本,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人艺派了于是之等协助他,后来没有写成。我想,不是写不出,是不肯将就。曹禺亲口对我说:「写戏是清苦的,你要坚持下去。」

有一次在黄永玉叔叔家,他兴致地拿出一幅竖版行书给我看。上面写的是曹禺的话:「戏散了,人都走了,我竟爱那空荡荡的剧场。」我很有同感,不论在国内还是去海外,到了一个地方就想看剧场,人在剧场里,好像心和魂都踏实安宁。人们都知道黄永玉曾经写信,毫不留情批评曹禺后期的作品,他诚恳接受,这就是他的真诚。我理解他那种刺心的痛苦,想写的写不了,不愿意写的又没有办法。可能是共同的职业,我很理解他的心态,所以对写出好剧本的年轻人他特别看重。写剧本艰苦孤独,但我像他一样迷恋舞台,痴情于这一份孤寂而又独特的工作。

他去世时,我在香港。后来我去了北京万安公墓,拜祭曹禺院长。好干净的一块石碑,碑上只有巴金写的两个字「曹禺」。不用太多的词语,黑泽明说,要讲清楚一个人很难,但他的作品说明了他的一切。
(本文图片由何冀平提供。何冀平为舞台戏剧、电影电视剧著名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