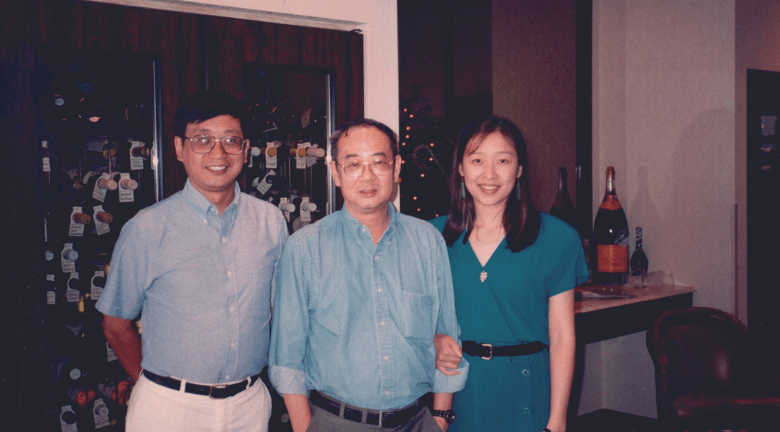編按:為了讀書「櫛風沐雨、宵衣旰食」,最終成為劉紹銘關門弟子的作者,撰文回憶恩師的點滴話語、拜師的經歷,分享當年在麥迪遜時師生間的往來,並以此文承載對恩師的懷緬。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二○二三年一月四日零點四十二分,突然收到恩師劉紹銘夫人司徒秀英的來電:「教授最後了,你要看望他就快來吧。屯門醫院E1病房。」我風馳電掣趕去了醫院。劉教授的學生們都來不及送別了,我能代大家看到他最後一眼,按說應該心安了。病榻上的他命如游絲,我輕聲呼喚着,好希望他還能再聽到我的聲音。過去三十年的師生情誼,一幕幕宛如眼前,恩師風采依舊,為人真情俠義、善良篤厚;文章莊諧意趣、妙語橫生。面對紛紛擾擾的繁華世界,他淡泊名利,抱持着文人風骨。似水年華,任憑煙雨。
夜深,失眠。腦海裏響起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老師周策縱教授的詩:「春雨初來君已去,小湖冰退尚無詩。」教授仙逝,三十年來的點點滴滴,讓我心裏滿滿是思念和傷感,久久無法釋懷!感恩有王德威師兄的越洋分享,談及我們各自當年在威斯康辛大學和劉教授的結緣,中與西、城與人、師與友……細細道來,也談到幾日後我們要送悼念鮮花的配色……沐浴在他言語的溫暖裏我漸漸復甦。我再次體悟到恩師給予學生這生命中的豐盛,四時山色,在在令人留戀、惆悵。這紀念文章僅僅二千餘字的空間,又如何能承載我對恩師無盡的思念?
為了讀書背水一戰

一九九二年,我辭去了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大學的工作去讀研究所。那時收到了印第安納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的錄取通知,可是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歐陽禎教授極力推薦我去跟劉紹銘讀書。他說,當今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是美國漢學的重鎮之一,而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劉紹銘教授是那裏最出色的學者,最難得的是他也是小說家和翻譯家,同時也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人。他學養豐厚、知人論世、很有個性。不過,他收不收你,就看你的造化了。就這樣,我決定去威斯康辛追隨恩師讀書。恩師收生甚為嚴格,因為我的本科專業是漢語語言學,恩師不肯馬上收我為門生。於是開啟了我漫長的背水一戰。那之後的幾年,我選修了劉教授所有的課,按照劉教授開的書單,篇篇研讀並給教授寫讀書筆記。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經濟狀況與今天的大陸留學生有着雲泥之別。那時來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都很窮,威斯康辛大學雖然是美國州立大學的常春藤名校,但是給文科學生的獎學金卻十分有限。威大東亞系的獎學金只有教中文的助教獎學金。在來威大之前,我作為中文老師已經在北京大學、美國佛蒙特明德學院、俄亥俄歐柏林學院等任教七年了,可是,在威大我卻申請不到教中文的助教獎學金。劉教授開導我說:「你知道嗎,你是『北京』來的學生嘛,這個我就沒辦法幫你了。如果你真的想讀書,我相信你會想到辦法的。我也打過工,做過餐館侍應生。」於是,他送給了我他的《吃馬鈴薯的日子》。為了跟教授讀書,櫛風沐雨、宵衣旰食,都是值得的。於是,從一九九二年到九五年,我每周有三晚在麥城一家中餐館Royal Garden打工。那時,香港著名作家、文化評論家馬家輝就是我們餐館的常客之一,他慷慨的小費是幫了我的學費的。
教授們的「家宴」
讀書之餘,最讓我難忘的是到老師家裏聚會。那時威斯康辛的教授們都有各自的「家宴」。比如劉教授家是典型的北美BBQ,烤爐上的雞翅、牛扒滋滋地冒着油花,師母向學生們分享着如何自製BBQ調料,劉府客廳裏放着港台歌曲,而地下室門上掛着的是李小龍的海報。語言學家鄭再發教授的家宴是地道的中國滋味,苦寒的麥城裏難以品嘗到的各種台灣小食,還有那特別治愈的暖暖糯糯的紫米粥,都令人難忘;系主任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教授家是太太拿手的墨西哥菜,席間聽Cutter教授分享墨西哥異趣橫生的鬥雞文化。周策縱教授的家有個悲涼的名字叫「棄園」。他的家宴是把學生請了來,他給出如何燉雞湯可以沒有油的理論,然後策劃指揮我們做飯。我最怕的是去漢學家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Nienhauser, Jr.)的家「雕蟲齋」了,他請了一眾學生聚會,席間常常會爆冷門。比如說,《穆天子傳》是偽書嗎?有什麼理據?在他家我總是提心吊膽,吃的什麼是不記得了,只記得十分羨慕呂宗力師兄和我的同學陳致對這些問題總有答案。我在威大的求學歲月過得十分充實,在師生傳道授業的關係之上,透過種種家宴,我能感受到更多了一份父輩般妥妥的呵護、期許和責任。
筆下有江湖,也有人間煙火

劉教授除了在威大治學授業之外,他還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創作天地,而他的翻譯作品,是二次創作,以賦予原作異國他鄉的生命。劉教授有入世的情懷和出世的筆觸,他把人生看得透澈澄明,把人心不古、世態炎涼幻化為荒誕不經、天馬行空、詼諧俏皮、古惑鬼馬的文章。文字時而俯仰生姿、低迴婉轉;時而詼諧幽默、雅俗共賞;時而聲氣激盪、俠骨錚錚。梨花淡白柳深青,許多感人的文字不失童心、真誠與自然。恩師的一支筆把人生的苟且寫出了瀟灑,他筆下有學界的江湖,也有人間煙火,真是妙趣天成。「劉紹銘體」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在寂寞中一往情深地綻放着,他的創作、譯作,文學評論、散文和雜文,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具有獨特個性的精神財富!
東輝今生有幸成為您的關門弟子,師生一場三十載,那是怎樣的緣份啊!吾師千古!我將懷着對恩師永遠的懷念與期許繼續前行。
(作者為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
愛才的劉教授 ●舒 非
那天我從群組訊息中得知劉紹銘教授大去,心裏突然覺得像缺掉了一塊,希望這不是真的,可是又不能不相信。呆坐了好一會,才掛電話給劉教授的夫人司徒秀英老師,本意是要安慰她,可說着說着,兩人卻在電話裏痛哭了一大場。
認識劉教授近四十年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我在香港三聯書店當編輯,老總潘耀明先生策劃出版《海外文叢》,約了劉教授一部雜文稿《遣愚衷》,稿件由我負責跟進,由此跟劉授書信往返,結上了文字緣。後來他來了香港,我們才真正見到面,開始了一段忘年的友情。

高山仰止
劉教授是國際級的名教授、名作家、名翻譯家和大學者,在文壇地位超然。他參與翻譯夏公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簡直就是中國近代文學的「聖經」。所謂高山仰止,因此我初次見到他時,難免有點誠惶誠恐,可是交往下來,只覺他溫文儒雅,謙沖平和,對我這小編輯的話都仔細聆聽,毫無大教授的架子,讓我如沐春風。其後交往多了,我們之間變得不光是業務上的往來,而成了經常相聚的朋友。
和劉教授相比,我自然是個末學後輩,因此他和我,可說是亦師亦友。不過他這個師,卻並非嚴師,我從來沒見過他疾言厲色,和他相處,我都可以放言無忌,不用擔心冒犯了他。因為我覺得,即使我說錯了話,他也會一笑置之,絲毫不會介懷。
劉教授二十多年前決定離開美國,回港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長,因為他的聲望,使嶺大的地位提升了不止一個台階。記得他召集主持的嶺南大學張愛玲學術研討會,可說是香港文學界多年難得一遇的盛事,殿堂級的學者作家濟濟一堂,連「神級」的夏志清教授也難得蒞臨了。還有白先勇、王德威等名家的講座,要不是劉教授的個人魅力,想不出有誰能吸引到如此多的名家遠涉重洋到偏處一隅的屯門來。
我總覺得,回香港任教和生活,對劉教授是極為適合的選擇。他名滿學術圈,足跡遍天下,任教過不少世界一級院校。但他到底心繫生他育他的香港,只有回到他的「故鄉」,他才真正如魚得水。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文化,同聲同氣的學生,不但讓他在教學和研究上揮灑自如,也刺激了他的創作思路,使他寫出了不少文貫中西、妙語如珠兼有港式味道的散文。
愛才惜才

劉教授苦學成才,大概因為自己的出身和經歷,知道文人出頭不易,他特別愛才和惜才,非常珍惜有才華的後輩。
大約是在九十年代吧,他讀到雜誌上一篇寫父子看足球的短篇小說,擊節讚賞,來電話問我認不認識作者顏純鈎,我說認識啊!結果我介紹他倆認識。自此,劉教授和顏純鈎成了莫逆之交,還一起合作編過許許多多有分量的書,在顏純鈎任總編輯的天地圖書出版。這是我這輩子做得最成功的「牽線人」。
黃子平教授是另一例子。八十年代,黃子平和李陀為香港三聯編了一套《中國小說》年選,劉紹銘教授非常欣賞,不止一次對我稱讚選家的眼光,對黃子平寫的序言,更讚口不絕。黃子平教授後來也跟劉教授成了好朋友。
我從三聯退休之後,到香港中華書局任資深策劃編輯。二○一二年是中華書局百年店慶,總經理趙東曉先生希望組織一套紀念文集,我建議出版《香港散文典藏》,讓劉紹銘和黃子平合作。名單是他們兩人商定的——董橋、劉紹銘、林行止、陳之藩、西西、金耀基、羅孚、小思和金庸。囊括香港九大散文名家,作者陣容一時無兩。
計劃中本來由劉教授和黃子平同掛主編之名,後來劉教授對我說,他掛顧問銜,讓黃子平一人當主編就可以了。理由是出版社要付酬給主編,顧問則一般無須付酬,這可以讓黃子平多拿點酬勞。香港出版艱苦經營,主編費並不多,劉教授對後輩的關愛,令我非常感動。
還有個好例子是王璞。王璞的小說和散文寫得非常好,又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她曾在嶺南大學中文系任助理教授,是劉教授的同事。有時候,顏純鈎和我,跟劉教授一起飲茶吃飯,他經常跟我們稱讚王璞的小說散文,還將讀過的精彩之處說出來,談得興起時,幾乎是眉飛色舞。
因在屯門工作和居住,出香港市區一趟,舟車勞頓,對年逾八旬的劉教授來說並不輕鬆,因此他並不常「出城」。但劉教授極重感情,假如他要來港島,會事先約朋友們見面,約得最多應該是顏純鈎和我。也有幾次約了蔣芸、黃子平、顏純鈎和我一起到中環的嶺南會所吃飯。吃飯聊天飲紅酒,我們和劉教授度過不少美好的時光。
劉教授非常關心香港的文化圈,經常留意本港的文化動態、關注文學雜誌以及報紙副刊,常常感慨報刊的文學副刊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最後的見面
最後一次跟劉教授見面,是二○一八年的九月十二日。顏純鈎要移民加拿大,約王璞和我去屯門向劉教授道別。本來說好要進屯門請劉教授的,不料反讓劉教授付錢做東了。
這幾年疫情肆虐,跟劉教授只能通電話,未能見面,時時在想,不知何時再能請劉教授吃他心愛的乾炒牛河。前年,司徒老師來電告知,她和劉教授要登記結婚了,我真為他們高興。我對司徒老師說,想進屯門觀禮,我先生可以為他們拍攝婚禮照片。不過後來司徒老師說,因為疫情嚴重,還是先不要見面吧,沒想到那次沒見上,就再也見不到了。
這件事,可說是我永遠的遺憾吧。
(作者為香港作家,曾任香港三聯書店策劃編輯。)
悖 論 ●吟 光
你是稀薄又穿透的太陽
破開二月的冰,卻裹挾滿身霜雪
舒緩與尖厲的和音
安撫不羈的魂靈,又教唆它更加不安
溫柔與暴戾的私生子
以身沉溺入火,再推開月亮與風
是夢,又不僅是夢
還是造夢者,是夢的造物主
不是玫瑰,摘下
便有了滿屋芬芳
是天邊那盞燈,壓迫靈魂的光
聲色輕輕,但是響徹——
擊打我失去了語言,只剩滿目瘡痍
今日與昨日決然不同了
宏大的波紋蕩起,整座湖面燒成傾巢覆滅的火
我可以手握玫瑰
但要怎樣,才能摘下一盞燈塔?
烈焰燃起,我永遠會失敗
星河漫爛,且寂寥
而火凝結成光,永遠會傳遞、滂湃
(作者為青年作家,出版有《上山》、《天海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