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月香港藝術發局頒發「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其中最高榮譽大獎「終身成就獎」得主為著名作家張彥(西西)。西西對香港文學藝術貢獻良多,屢獲獎項,寫作近七十年,早年作品多在報刊上發表,其小說、新詩及散文均備受肯定。為表慶賀,今期一起讀西西。本版邀得西西研究專家何福仁,從西西幾本近著說起,細探西西的文學藝術、成就,以至多元創新、「工夫深處漸天然」的風韻。同時選刊西西一篇重新修訂後首度發表的小說,不可錯過。「綜觀西西漫長的創作歷程,可見她是一個長跑者,她的作品歷久不衰,她的寫作表現手法也不斷在翻新……」本刊總編輯潘耀明漫談西西的鱗爪。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關於西西的鱗爪 ●潘耀明
要我來寫西西,很有些牽強,我與西西從未真正交往,只在朋友聚會中遇見過一、兩趟。倒是她在二○○五年憑《飛氈》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頒授第三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我是終審評委之一,其時才開始涉獵西西的作品。她因身體欠適,沒有赴會,那一座沉甸甸實銅打造的獎座是由我捎回香港,由何福仁先生轉交。
如我沒有記錯,西西是在香港嶄露頭角、在台灣崛起的香港作家——她早期的作品,不少是在台灣的報刊刊登。一九八三年她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獲台灣《聯合報》第八屆全年最佳小說獎,此後多次獲獎,可以說,西西是在台灣成名,其後香港及內地評論界才側目相看,這已是多年後的事。
換言之,西西真正的伯樂是台灣《聯合報》著名詩人、副刊編輯瘂弦,是他較早關注西西的。何福仁在〈西西的幾本新書〉一文指出:「西西是『香港製造』的作家,可同時是台灣作家,甚且是中國內地作家。換言之,她從我城出發,打通特殊與普遍,其成就並不專限於某一時一地。」
無疑,西西是made in Hong Kong,她之成名,也是由外銷轉內銷。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西西獲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發「終身成就獎」,可說是名至實歸。
香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壇,大都是南來作家居多,蕭紅、張愛玲、端木蕻良、戴望舒、許地山等名作家,大都是以香港為其創作基地,成為一時瑜亮。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香港各大、中學校紛紛成立文社潮,這一時段的文社潮成為產生香港本土作家的土壤。這一期間湧現了一批香港本土作家,西西是其中佼佼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稀方指出:「在香港的作家中,西西可稱得上是最具本土意識的作家。『香港意識』的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的工業化城市化而滋生的『我城』意識,二是八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九七』回歸的迫近而引發『失城』意識。可以說,在這兩個階段中,西西的小說都堪稱代表。」可謂是一矢中的。
綜觀西西漫長的創作歷程,可見她是一個長跑者,她的作品歷久不衰,她的寫作表現手法也不斷在翻新,從這期《明月灣區》何福仁選輯的兩篇西西跡近寓言的小說,也可見一斑。
(作者為《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西西的幾本新書 ●何福仁
這一年,我們看到西西三本新書,《石頭與桃花》、《動物嘉年華》、《西西看電影》上冊,倘加上稍早之前的《欽天監》,則是不同面向的大四喜。之前她在內地的兩本簡體版﹕《白髮阿娥及其他》以及重印的《飛氈》,都頗受歡迎,誠如不少論者指出,西西是「香港製造」的作家,可同時是台灣作家,甚且是中國內地作家。換言之,她從我城出發,打通特殊與普遍,其成就並不專限於某一時一地。
西西創作與電影的微妙關係
《西西看電影》一書是上中下三冊的上冊,據說中冊會在年底出版,之後是明年初。這是年輕學人趙曉彤努力發掘的成果,她不辭勞苦,起出西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各刊物的電影專欄,包括《新生晚報》、《中國學生周報》、《真報》、《星島晚報》等等,這些刊物都久已休刊,西西自己也沒有剪存。有的,譬如《香港影畫》的「開麥拉眼」,當時已相當矚目,及後重溫,仍備受讚揚,「情文並茂深入淺出」云云,如今知者已少;至於《亞洲娛樂》上的電影專欄,則連西西也不復記得,可每期都有她的中外影評,有時多達七八篇,用上不同的筆名。這些,在中或下冊可以讀到。她無疑是香港引介西方電影的元老之一。她緬懷當年加入第一影室電影會,每星期到大會堂看電影,像讀書上課,「這是香港的好處,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新最好的電影,……在那裏,我會看到林年同、金炳興、羅卡、陸離、石琪這些同學。」

而新潮電影的手法,啟發她的創作,她第一本小說《東城故事》(一九六六年;其後收於《象是笨蛋》),書名回應歌劇再拍成電影的West Side Story(港譯《夢斷城西》),從西而東,最大的特點即是運用電影的手法,儼如電影劇本:割、轉位、淡出淡入,還說明背景音樂。小說分八節,各以第一身「我」出現,而呈現不同的視覺。在小說裏轉化電影技巧,《東城故事》明顯而易見,更多的則是潛移默化,融入了各種寫作之中,例如《春望》(一九八○年),全篇對話,對話之下加上家務、兩地親人互訪等具體敍述。書中的對話除了傳統的你一言我一語,一人一句,另闢其他三種,要求讀者從說話內容辨別:一、以對話轉接不同的時空;二、一人可以連說好幾句;三、一人(老人家)似跟人對話,實為自我的沉吟。限於篇幅,這裏只能約略闡述第一種:內地開放之初,母女倆談話,母親說到和親妹兩地分隔二十多年,向女兒查問回內地探訪的情況,馬上剪接為女兒和姑母當時的對話,這即是電影轉場(Transition)的手法。
西西的創作與電影的關係殊深,早期對電影的論述,也有啟蒙的作用。然則研究西西,以至研究香港電影文化,豈能錯過。
動物與詩的嘉年華
至於其他三本,我多少都有幸參與。首先是《動物嘉年華》。西西一直希望出一本繪本。這一年我整理她的文稿。其中詩作,部分有關動物,於是想到,何妨選出一本以動物為主題的繪本。她以往發表過的詩,不乏抒寫動物,但出了書就不選了。結果選出二十三首。繪本不厚,但不妨中英對照,於是請名譯家費正華(Jennifer Feeley)襄助。她譯過西西詩集,曾因此得獎。最近企鵝經典(Penguin Classics)要譯西西的《我城》,也屬意費正華。

這本《動物嘉年華》的詩,除了一首〈水母與蛞蝓〉,其他都作於近年寫作長篇《欽天監》期間。在以往,她可以自己繪畫,她的《我城》、《飛氈》,都是自己配圖。我想到這一次可以找不同的畫家去繪畫,一人一首,較長的詩,可以多幾位去畫。我問她可行嗎?她說很好,比自己繪畫更好。當年創辦《大拇指周報》(一九七五年),有一版叫「大家寫」,名字是西西想出來的,這次她叫大家畫。而這正是嘉年華的精神,並且呼應西西詩作平易親人的風格:大家參與,不論專業畫家、業餘愛好者,只要有興趣畫、能畫,就可以參加,齊來關心異類,尤其是弱勢者。我在臉書上詢問有哪些畫家願意為西西的詩配畫,立即有近三十位聞風主動參加,此前我大多並不認識。又另有朋友介紹好幾位。我不看名氣,只參考畫家已有的作品,有四五位遲來了,只好當遺珠。
西西的詩,我在書裏的前言已略述一二,要補充的是,她的詩,別樹一幟,既久已告別五四的新詩,又不宜以當下一般玄奧晦澀的現代詩觀之;不難,可又不淺,往往是從具體微細處切入,從實入虛,再化實為虛,言近而旨遠。一些朋友會想到波蘭的辛波斯卡。其實西西讀辛的作品是在辛獲諾獎之後,之前也許略讀過。西西當然很喜歡,她倆確有相似之處。不過西西的風格多年來早已形成,遠在編輯《中國學生周報》時已可見,她喜歡選用當時兩位寫得比較明朗的年輕人,羅卡曾指出,其中一位是也斯。其他的,她自稱大多看不懂,因而辭職。
齊白石題畫云:「工夫深處漸天然」,這是西西詩作的寫真。她的詩齡超過六十年,多年來心力雖表現在小說,不過詩文互通,同樣的工夫,不可謂不深,固然一以貫之,可也不是一成不變,是變得更闊廣更多的關懷,寫得更素淨自然。
寫作《欽天監》期間,寫詩無疑是一種舒緩、調劑,這長篇斷斷續續寫了五年。二○一七年,定稿之前,她提出要重訪北京,看看故宮、古觀象台、幾座教堂等等。當她走上古觀象台的斜階時,不用攙扶,算算,原來已經八十歲了。她甚至想到長城,雖明知已經人工化,仍然希望走進那種「虛擬的實境」去,用她自己在後記的話:「讓我在現場有一種靠近歷史的幻覺」,終因舟車太勞累,放棄了。
豐富多元具創新的《欽天監》
《欽天監》的內容非常豐富,可從各種角度閱讀,我也寫了篇〈對話:敍事者與受敍者〉在《讀書雜誌》第三期上發表,這書寫法上我以為有兩個特點:以「對話」為經,「引文」為緯,而經緯互通相接,此說當然也是書中所云一種「假想線」。全書的對話主要是周若閎與容兒,兩小無猜,後來成為夫妻。對話既可作為長篇敍述之後的間場,也有承傳點撥之功,富於情趣、幽默,最後以兩人的對話收結,又餘音裊裊,令人感慨。書中傳教士來華,也是一種中西文化的對話,又各自產生內部意識不同的對話。看來唯有互相聆聽、彼此尊重,對話才有意思。書中人物,種族多元,外客背景不同,國內則漢滿蒙,其中描述三位同窗,性格各異,各有發展,尤為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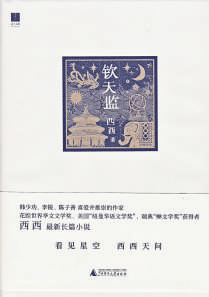
繁體版,右為簡體版
若閎是小說的敍事者,通篇固然是他告訴容兒自己的「所學所見所聞」,她是受敍者、接話者。不過可不是消極的被動,她也提出意見、鼓勵,甚至修訂他的談話(文中曾提例證)。然則她同時也參與創作,不啻同時是敍事者。容閎二為一體。而這些對話,其實也面向讀者。這是若閎對忘年交趙昌「歷史不是普通人寫的」的回應。趙昌實有其人,是康熙親信,為養心殿總監造,並負責接待傳教士。
若閎大半生在欽天監內工作,專責觀天,但觀看世情時局,不走出宮監之外,則仍是坐井。後來他參與考察長城,繪畫地圖,是出井的一步。再然後終於走出宮禁,真正認識歷史的軌跡、民間的甘苦。
這書每若干節之後另附「引文」,這是形式上前所未見的創新。有些論者以為這是作者西西的附錄,不是的,這是若閎的「手抄」,是小說的有機組合。臨末離開京畿時,他提出書不用帶,要用的都手抄起來了,稍後又說輾轉好些地方,總不忘讀書,且無所不讀,從蒲松齡、劉獻廷,到黃宗羲……,他要追回失去的記憶(一二九節);引文即從蒲、劉開始。這是他抽離後重新對世事的閱讀,毋寧也是他跟當下史事的對話,寄寓了他的「所想」。若干引文,例如傳教士的記述、清代的檔案,當非時人可知,這是康熙同一時期後設的參照,而並沒有超出敍事者對歷史的水平接受。這畢竟是小說。
易言之,若閎是敍事者,可同時是受敍者;他是書中作者,可也是讀者。而所引之文,跟隨情節的發展,反映閱歷漸次遙深;敍事的語調、角度,也因應年紀增長而變化,慮念多了。所以,這書也可以從「成長小說」的類型看,分別在主人翁經歷種種事件之後,取向迥異。
《石頭與桃花》則是短篇小說集,收未曾出書的新舊作,又以新作佔大半篇幅。其中〈土瓜灣敍事〉,二萬六千字,已近中篇,西西用小說、詩、散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寫那麼一個地方,充滿情味,有趣,又大不乏自嘲精神。之前她曾以這地方做背景,寫過長篇《美麗大廈》(這是西西比較「難讀」的書,台灣小說家王禎和過世前卻認定是西西最好的作品)、短篇〈陳大文搬家〉(收於《白髮阿娥及其他》)。在西西筆下,其實處處可見這地方的影跡,這書起首第一篇〈文體練習〉,所寫的場景,也是土瓜灣,寫得從容,淡定而內斂,毋寧也是「工夫深處漸天然」。加上過去的《我城》、肥土鎮的系列故事、《浮城誌異》等等,她為香港這特殊的城市塑造了一個豐富而深刻的文學形象,從微觀到宏觀,或寫實或虛構,其價值一時未敢完全斷定,其意義則肯定不下於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以至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馬孔多。
今年藝術發展局頒給她「終身成就獎」,誰說不宜?

西西短篇小說集《石頭與桃花》,二○二二年。
(本專題圖片由何福仁提供。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



